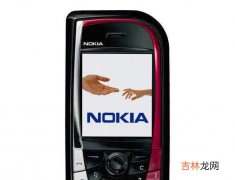|冰点特稿:三十立什么( 三 )
邱领上学时的“责任”是做一名好学生 , 甚至连文娱活动都属于履行责任——那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人 , 是发展自我的一个步骤 。
小时候她拉小提琴 , 父母选的 , 大人每周骑车带她去老师家里 , 回家逼她练琴 。 她不喜欢 , 把琴摔了 。 家人要求她必须学一件乐器 , 她挑了竹笛 , 考到了十级 。 “这东西是我自己选的 , 相当于跟我妈做了一个交易 , 我绝对不能放弃 。 ”
有一年寒假 , 快过年了 , 邱领还在做作业 , “我就特别崩溃 , 在院子里面转圈 , 转着转着就很生气 , 一下就把手机砸到地上了 , 当时还是翻盖手机 。 ”
母亲看到了 , 说“你这样做真的非常没有礼貌” 。 邱领对那个瞬间记忆深刻——家人关心的居然不是自己为什么砸手机 , 而是这样做有没有礼貌 。
去年确诊抑郁症后 , 邱领去做心理咨询 , 哭得不能自已 。 她原打算用两三个月快速解决情绪问题 , 回到正轨 , 却发现了许多之前从未被当成问题的问题 , “我才发现自己对于父母有很多怨气 , 原因在于我没办法展示真实的想法和情绪 。 ”
从小到大 , 当她展露真实需求的时候 , 总会被反驳和否定 。 “我周围的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沟通问题 。 ”
她有一个小本 , 里面记录了自己以后当父母要怎么样做 。 其中有一条是“我会非常尊重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
邱领虽然不认同父母的做法 , 但也理解他们 。 她的父母是“非常努力向上冲的人” , 是她从小的模板 。 他们最初受惠于体制 , 又在转向市场的波动中完成阶层跨越 , 他们身上既有不服输的冲劲 , 又有对规矩的尊重 , “对于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在他们身上是混合的” 。
到了下一代 , 子女拥有更多选择 , 他们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 , 强调个体的感受 。
邱领就读的史密斯学院 , 坐落在美国东北部 , 在一片叫先锋谷的地方 , 校友有两位前第一夫人、《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教会美国人做饭”的美食家茱莉亚·查尔德等名人 。
冬日暴雪 , 学生们窝在宿舍里烤火 , 或是去图书馆搞论文 , 守着学校的天堂湖 , “我们从未怀疑过天堂里的生活 。 ”
漫长的历史里 , 这所女校曾教淑女如何在火车上优雅地放行李箱 , 如今在油画课上 , 一位女生用经血作画 , 大受好评 。 “老师不教你画画的技巧 , 只说主题 , 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自我表达 。 ”
入学前 , 学校的推荐书目是《天空的另一半》 , 讲述亚非拉国家女性的生存困境 。 课堂上 , 哲学、政治学、脑科学三门课火爆 , 虽然它们读起来很累 。 有一年暑假 , 邱领想学法语 , 学校出钱把她送到巴黎学习 。
“学校给我树立了美学价值和人文价值 , 我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灰色地带 , 但是关于知识和灵魂的需求还是有好坏之分 。 ”邱领说 。
回国后 , 每次跟女校的朋友相聚 , 她们给的精神上的支持能帮她“顶住一个又一个生活中的脓包” 。
邱领裸辞后 , 见了十几位好友 , 包括校友 , 发现许多人都面临情绪问题以及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问题 , 在倾诉中彼此消解痛苦 。
危机最常出现在即将30岁时 , 第一份工作和第二份工作的交接期也是一个重灾区 。 这两个节点 , 很多人选择裸辞或是把老板炒了 , 去一个陌生的环境 , 像放飞关久了的鸟 。 “高度相似的人生经历 , 在我朋友圈里面 , 在过去这一年被重复 。 ”
邱领说自己内心孵化出两个小人 , 一个白小人很闪亮 , 是“爸妈说、社会说”的正确答案;一个黑小人代表自我意识 , 是小时候的调皮、是冲破束缚 , 也是反抗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给娃压岁钱,三十和初一哪天好?这里大有学问,许多家长给错了!
- |知青往事后续:三十年后见到亲生女儿,她心里十分愧疚
- 相亲 女人三十五之后,越是学会主动,幸福才能越靠近你
- 坚持写了三十多年日记,给我带来了诸多益处
- “三十岁的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三十岁还迷茫?太正常了!
- 李秋月|知青往事:三十年后重回陕北,见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他万分愧疚
- 爱情|其实,女人的好运,是三十岁后到来的
- 彩礼|“彩礼三十万,最后一次机会”“我花了十万,找了比你好的”
- 爱情 女人的好运,是三十岁后到来的
- 婚姻|我被一个三十多岁的未婚女孩,给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