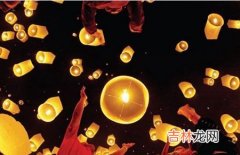“允许自己不快乐”:快乐是一种能力吗?( 四 )
正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言 , 景观化的存在把人牢牢控制在影像幻觉之中 , 从而将人类权力流放到一个彼世的技术实现 , 那是一个“虚假的天堂” 。 而滤镜的“虚伪”之处正在于其对“幸福监视”的认同 , 进而以套路化的美丽与批量生产的幸福模板覆盖了真实、具体、有所分异的面孔、处境、经验与心情 。 在这样一种展演状态中 , 真正的交流渴望也时常演变为经由他人的赞赏完成的对于“我快乐 , 我幸福”的自我确证 。 而滤镜由显到隐、由外在到内置的过程则或许更为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的精神状态与行为模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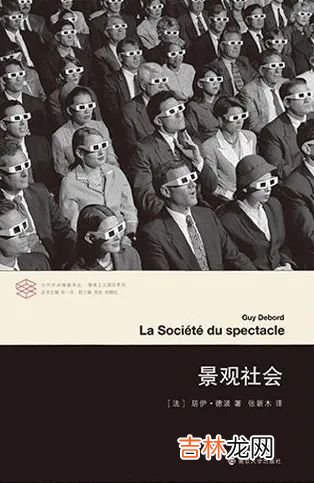
文章图片
《景观社会》 , 作者:[法]居伊·德波 , 译者:张新木 , 版本:折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
这可能导致迪富尔所谈到的“被他人需求绑架”这一心理困境 。 “即使内心怒不可遏 , 也要面带微笑 , 和蔼可亲 。 越是被别人的需求绑架 , 就越是远离自己的渴望 。 在与自己并不相符的所谓现实中越陷越深” , 凡此表述不难让人联想起我们熟知的“讨好型人格” 。 在此种“人格”状态下 , 自身所为仿佛大半被他人的喜好与需求驱动 , 对于有讨好倾向的人而言 , 生活与社交或许殊为不易 。
然而值得辨析之处在于 , 所谓的讨好是否基于对他人的真正“关注” , 又或者 , 他人的评价已然成为“讨好者”内置于自我心理世界的又一面滤镜 , 人们将此作为自身“完美”的确证 , 一面以迎合他人为由逃避着真实的自我感受 , 一面惴惴于完美形象的可能破损、无力维系 。
与“滤镜”相似 , 在逃避不快乐的种种方式中 , “沉迷”也是一种具备文化症候性的行为取向 。 如果说滤镜代表着向外的展演 , 那么沉迷则更多地意味着向内自处的状态 , 承载并制造着“原子化”社会情境中众多个体快乐与不快乐 。 从工作学习(“沉迷工作”)到消遣娱乐(“自得其乐”、“玩物忘忧”)再到酒精与药品(“酒精、麻醉品和过度劳累”) , “沉迷于xx”的生活方式提供着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镇静剂” 。
而比起对所沉迷对象即“外物”的依赖 , “沉迷”这一状态的更深刻意义或许体现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一个完全属于“自我”的空间 。 在这个安全岛或舒适区内 , 个体似乎得以暂时摆脱“他者”的监视 , 进入“内心世界” , 获得哪怕暂时性的愉悦与平静 。 在此 , 迪富尔再度提出了不无严峻性的问题 , “或许可以问一问自己 , 自己对某种活动执着 , 究竟是源于它带来的满足感 , 还是害怕停止这一活动后出现的情绪 。 换句话说 , 是快乐的驱使还是不快乐的逃避?答案可能是在两者之间” 。
事实上 , 当我们沉迷于某种活动 , 无论是生产性的工作或是消费性的消遣娱乐 , “追逐快乐”与“逃避不快乐”两种心理倾向往往并置出现、相互渗透:主动的创造与被动的躲闪、对幸福的探求与对不幸的遗忘、以自己所熟悉和喜爱的方式与世界发生更多联结的渴望与“遗世独立”拥有一个安静的“小世界”的需求 , 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沉迷”的表象下塑造着现代人复杂流动的心理世界 。 在沉迷的状态中 , 真实情感的生产、投注与压抑、驱逐仍然并存 。
如此看来 , “沉迷”同样不只具备负面的情感价值 。 迪富尔以“沉迷于外物之中 , 逃避自己的不幸”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现象和巨大悲剧” , 却多少忽略了在此种沉浸式体验中个体重塑物我关系的尝试 。 所谓“玩物忘忧” , 不单是逃避自我 , 其实也是一个感知、认识自我的过程 。 因此 , 或许也不必对这一时代悲剧抱以过于绝望的态度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女人梦见有人要害自己的预示介绍
- 练字如何自己练好一点
- 梦见自己抱小孩的寓意
- 耄耋与什么字同音
- 致拼搏路上的自己短句 致拼搏路上的自己短句有哪些
- 婚姻|“听说,没有一个女人能活着从老公的手机里走出来……”
- 清热生津|“允许自己不快乐”:快乐是一种能力吗?
- 诚信格言 关于诚信的格言
- “娘家弟媳怀三胎,我劝她不要生,没想到得罪了一圈人”
- 致自己微信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