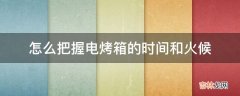郭红出书 周国平妇唱夫随 谈谈“何为向往的生活”( 二 )
尽管如此 , 周国平坦承以前并不看好郭红写的东西:“说实话 , 我看不上眼 , 我觉得就是小女生写的东西 , 就是小情调 。 但是 , 她非常喜欢看文学作品 , 尤其是西方当代的一些作品 , 当代小说她看得比我多得多 , 有时候我听她议论几句 , 特别到位 。 那个时候我就说了 , 我说你应该写东西 , 把你文学上那种感悟到的东西表现出来 , 我觉得那个是有意思的 。 可是这一天我等啊等 , 始终没等到 。 没想到 , 我们被困在长岛的7个月里 , 这个日子来了 。 那段时间里 , 我看她老是坐在桌子前面 , 有时候夜里还在打字 , 我知道她在写文章 , 我想不就是那些小女生的情调吗?不用去看 。 后来我看她写得那么带劲 , 有一天晚上我悄悄打开电脑去看 , 一看我就惊呆了 。 她不再是那个小女生了 , 我就说 , 我看到的是一个作家 。 ”
周国平给作家的定义是“被文学附了魂的人”:“我相信每一个人内心有一个文学的魂 , 但这个魂经常是睡着的 , 她那个文学的魂醒来了 , 写得非常大气 。 我特别吃惊 , 可以说是喜出望外 。 ”
也因此 , 周国平笑说自己“举贤不避亲” , 非常坦然地为夫人的这本书写了序言:“给自己的太太写序 , 这好像是一件尴尬的工作 , 但我很坦然……她的作品和我的很不同 , 是更感性的 , 因此也是更文学的 。 她的写作刚刚起步 , 但已经是走在她自己的路上了 。 这正是我最欣赏的 。 ”
终于明白 , 什么叫活在当下
看了<长岛小记> , 周国平说他错过了郭红书中写的很多东西 , “我跟孩子比较谨慎 , 因为疫情 , 我们就尽量少出门 , 但她这个人闲不住 , 她是农村长大的 , 在家里呆不住 , 总要开车到海边逛 , 到森林里面逛 , 经常一个人去 。 大自然给了她灵感 , 我觉得她真的是属于乡村的 , 她和乡村是有感情的 , 其实长岛就是个大乡村 , 都是树林、大海、山 。 可是这些恰恰是能够把她以前沉睡很久的对自然的感悟、那种感觉唤醒了 。 这本书里面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一部分 , 她对自然的这种感觉 , 真的是很好 , 我肯定写不出的 。 ”周国平表示 , 滞留长岛既是一个意外 , 也是一个契机 , 在长岛这个寂寞与茂盛之地 , 看着这本书完成 , 仿佛看到一个小小的奇观 。 “她在自己的灵魂的旋律里走 , 从她的文字能听见这旋律 , 自由 , 灵动 , 旁若无人 , 把你也带进了这旋律里 。 ”
对于创作<长岛小记> , 郭红坦承虽然她陶醉其中才有所触动、有感而写 , 但是心里又无时无刻不在想逃离长岛 , 想要回到自己原来熟悉的生活中 , “我们逃离在外的时候 , 回望原来的生活 , 才发现它对于你那么重要 。 ”
困在长岛的那段时间 , 让郭红对“活在当下”深有感触:“我们有时候对周围是没有感觉的 , 走过这个街道其实你没有看到什么 , 你可能活在你的状态里面 , 什么也没有看到 , 都没有经过你的心 。 而我们在长岛时 , 我觉得眼睛像个摄像机一样 , 我看过什么好像都在脑子里了 。 ”所以 , 她在文中写道:“以前总是不懂 , 什么叫活在当下 , 现在明白了 , 就是随遇而安 。 其中最重要的是‘安’ , 尽快在新的境遇下保持内心的平静安宁 , 适应它 , 顺应它 , 择机而改变它 。 ”
捆绑在一起的关系最糟糕
有趣的是 , 郭红在书中有个标题是“‘浪’是每个人的宿命” 。 对此 , 她解释说:“我们通常都觉得男人更‘浪’ 。 比如古龙笔下的英雄 , 他们不断在寻找醇酒、美人 , 但我想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家的话 , 这个‘浪’不就是一种放逐吗?就永远这样下去 , 何时是归期呢?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呢 。 如果永远‘浪’下去 , 这是一种惩罚 , 而不是一种享受的状态 。 而且浪到最后 , 没有最浪只有更浪 , 你的人生不就是很虚无吗?寄托在这样一种不断的用别的东西证明自己的一种感觉上面 , 我觉得这是非常渺小的一种活法 。 但是 , 好像不少人都要经过这样一个情感变化的状态 , 好像你意识不到安定下来的价值 , 你在这种折腾、这种变化、情感的各种尝试之中 , 最后发现最适合自己的东西 。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孝老爱亲类郭红香郭红香 十佳好媳妇!毕节道德模范郭红香
- 周国平 心若晴朗,阳光和幸福一直在路上
- 周国平《人与永恒》:“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 一个悲伤的母亲,怎么能教育出一个幸福的孩子?
- 周国平 别怕,只是孤独
- 周国平说过:“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 如果这一生能遇到真心爱你的人,是多么的幸运
- 诗词有什么用处?作家周国平认为 严选课 | 人生不能只做有用的事,不妨读读无用的诗
- 周国平 靠自己,永远不会输!(说得真好)
- 周国平|人生最大的失败,并非无钱无势,而是至死也看不透这“两个字”
- 周国平 一个人最高级的心态:清静
- 周国平《把心安顿好》:“世上有一样东西 “凤凰男”的嘲讽:你既然选择要钱不要孩子,还好意思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