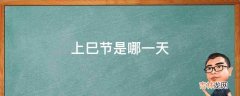|藤儿蔓儿总关情
藤儿蔓儿总关情
作者:张谨
第一节
上海人说:“三代不出舅家门” , 意思是外甥和外甥女长得会像亲舅舅 。 确实 , 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我的舅舅 。 所以当我和我的表姐妹们站在一起时 , 别人大多会指着我说是张大夫的女儿 。
我的少女时代有三年时光是生活在兰州军区所属的空军军校——西安空军002部队 , 我舅舅是军校的军医 。 文革时 , 军校里经常放映“批判电影” 。 有一次放映《战上海》 , 我和表姐妹们挤在大会堂的门口也想进去看 , 却被检票的战士拦住了 。 这时 , 有一名战士指着我说:“看那丫头的模样是张大夫的女儿 , 让她进吧!”结果我进去了 , 我的表姐妹们却被拦在了门外 。 因为她们长得像我的舅妈 。
大概因为我母亲这一支的祖先有西亚血统的缘故 , 我的舅舅年轻时很英俊 , 浓眉大眼、鼻梁挺直 , 穿上苏式军官服、戴上大檐帽时 , 就像电影里的皇家空军军官一样神气 。 记得有一年苏联红军歌舞团来华演出 , 电视里直播演出现场 , 我母亲过来一看就说:好像里面都是你舅舅!
我也发现 , 舅舅越老了越不像汉族人了 , 无论是相貌还是个性或是饮食习惯都不像标准的汉人 。 连我的表弟也越长越有胡人的模样——夏天光膀子时 , 只见他的络腮胡子卷曲着从两腮一直连到胸前 , 两只大眼睛上的长睫毛还向上卷曲着 , 真真让我羡慕不已 , 感觉这么长这么漂亮的睫毛长在男孩子眼睛上真的有点浪费了!
但是 , 长得像英皇空军的舅舅却非常喜欢国粹京剧 , 没事的时候就会哼哼几句 。 有一年舅舅到上海征兵时在我家住了几天 , 每到母亲下班的时候 , 舅舅就驮着我 , 唱着京剧一路迎出去接我的母亲 。 长大了再回想当时的场景 , 感觉很有戏剧成分:穿着苏式军官服的英俊舅舅 , 口里却唱着国粹京剧 , 背上还驮着个扎着中式羊角辫的女娃 , 该是何等中西合璧的模样!
母亲告诉我 ,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 为了保证我的营养 , 舅舅不时会把他并不优厚的薪金和糕饼票寄一些给母亲 , 并关照母亲一定不能让我们姐妹俩饿着 。 所以至今 , 每当我的同龄人怀着感慨的心情 , 回忆那扒拉着自制的秤杆做饭的日子时 , 唯有我却一脸的茫然 , 对三年自然灾害没有任何记忆 。

本文图片
“文革”开始后 , 学校“停课闹革命” , 而父母亲都受到了运动的冲击不能及时地照顾我 , 舅舅就写信给母亲 , 要母亲把我送到军校去生活一段时间 。 记得那天母亲给我念舅舅的来信 , 舅舅先是说了要让我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 , 然后说了部队的生活条件 , 说等我到了年龄就考虑正式入伍 。 舅舅告诉母亲一定要给我买卧铺车票 , 并一定要把我托付给列车员照顾 。 母亲按照舅舅的建议和嘱咐 , 第一次让我远离了她 , 把我送上西去列车 , 并把我托付给了一位列车员 。 与我相邻的卧铺位上 , 是一位回西安的出差干部 , 他对母亲说:他姓李 , 他也可以照顾我 。
记得一路上 , 每到一个火车站 , 都能看到头戴柳条帽、手持类似“红缨枪”的“文攻武卫”们站在站台上 。 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造 , 火车过江要分成几段由轮船花几个小时摆渡过江 。 从上海到西安的直达快车就要走整整30多个小时 。 到了西安火车站 , 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了 。 李叔叔带着我下车 , 在接站的人群中找到了我的舅舅 , 让我确认是我的舅舅后 , 二话没说就招手告别了 。
舅舅听我说 , 李叔叔自己掏钱给我补差额换了一张下铺的票 , 就一个劲地怪我没早告诉他 , 不然应该好好感谢人家的!现在想来 , 那时的社会风气还真是好 , 就像电影《兰兰和冬冬》那样 , 小小的年纪就可以自己坐火车去远方 , 不用担心遇到人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