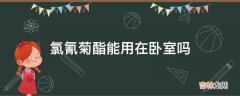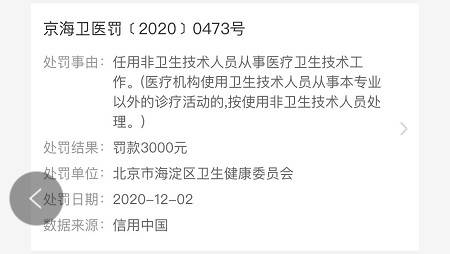本文图片
等我坐公交车 , 再步行好一段路赶到学校时 , 下午的考试已经开始了 。 监考老师很温和——那张和蔼的笑脸可以温暖我整整一生 。 听我简单地讲了情况后 , 她把我让进了考场 。 但成绩可想而知 。 接下来的几场考试也稀里糊涂地考完了……
考试成绩出来 , 除了第一科语文考试成绩还不错以外 , 其他的都较差 , 总分没有达到理想高中的分数线 , 但还是考上了两所中专技校 , 一所是美术类的 , 一所是财会类的 。 这当然不是我的理想 。 父亲不甘心 , 酷热的夏天 , 带着我去没有开学的学校考察 , 试图唤起我的进取心 。 大热的天 , 父亲穿着短裤 , 披着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衣 , 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 兼作遮阴 , 或扇风 。 父亲走在前面 , 我跟在后边 , 无精打采地走着 。 仿佛是钦差押着罪犯前往别地 。
父亲曾经当过教师 , 也知晓甚多 。 一路上 , 他跟我讲了许多道理和县城里的一些情况 。 可能是叛逆 , 也可能是执拗或倔强 , 我对那两所学校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 知道已无可挽回 , 父亲不再劝说 。 我跟在父亲身后 , 亦无语 。 这种无语 , 默默地宣告我纯粹的学生时代终结 。 夕阳下 , 我看见父亲曾经像山一样的脊背 , 微微有些驼了 。
那个时候 , 一些年轻人正在或者已经从土地上脱离出来 , 开始进城里打工 , 靠手艺在城里谋生、挣钱 。 我的二姐夫我喊二哥也夹杂在进城的人群中 , 他学的是木匠 , 同门师兄弟很多 , 相互帮忙或揽活一起做 , 是他们互相关照的默契 。 他和他的师兄弟们很快在这座省会城市站稳了脚跟 。
父亲与母亲商量 , 让我去成都跟着二哥学木匠 。 父亲征求我的意见 。 闲散的我岂有不同意之理 。
我初到成都的街头行走 , 东南西北不分 。 那时 , 成都的天空有点迷茫 , 我也迷茫 。
我跟在二哥身后 , 背着背兜 , 里面装着斧头、刨子、锯条、卷尺等 。 左拐 , 右拐 , 直行 , 到了九眼桥附近的一个路边劳务市场 。 二哥拿出一些工具摆在路边 , 以此招揽生意 。 和我们一样做木工手艺的人不少 , 还有刷漆、砌砖等手艺人 。 那时的生意并不好 , 少有人问津 。 其间 , 二哥接了一个木工师兄的电话 , 问我能否找到回去的路 , 我点头 , 二哥便离开了 。
天快黑了 , 没有接到活儿 , 我收拾工具返回 。 不知那儿拐错了 , 走岔了 , 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 倒回去再重走 , 依然 , 往复多次 。 我坐在街边 , 无助地哭了起来 。 哭完了 , 再找 。 等我深夜摸到住处 , 二哥早已回家了 , 锅里煮着白米稀饭 , 水雾蒸腾 。 我的那颗玻璃心 , 比稀饭还要稀 , 还要碎 。
我在成都大约呆了一个多月 , 就离开了 。 成都的天空没有表情 , 成都的阴雨也将我轻飘的脚步轻飘地抹掉 , 不留痕迹 。
后来 , 每次从郑州回四川老家资中 , 我都会在成都勾留几日 , 但从未想去过九眼桥看看 。 我不知道那儿变了没有 , 不知道那儿是不是还有招揽生意的手艺人 。 岁月不羁 , 那是我生命折叠中的一颗肉色青春豆 。
父亲决定亲自“带教”我 。 父亲没有技术 , 他只会勤奋地耕种土地 。 土地是他眼中的“宝” 。 物质生活的一切 , 他都伸手向土地要 。 土地对他也不薄 , 回馈他粮食、蔬菜 , 以及由这些东西换来的其他的物质 。 靠着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 , 父亲养活着全家9口人 , 日子过得有汁有味 。
坦诚地讲 , 父亲应该算是一个优秀的庄稼人 。 “优秀”这个词用在庄稼人身上 , 好像有些不搭 。 父亲站在土地面前 , 比站在我面前更有自信 。 父亲腰板挺得直直的 。 他有理由骄傲 。 土地听他的话 , 给他丰厚的馈赠 。 我也听话——尽管有些叛逆 , 但从不敢顶撞父亲 。 当然 , 这不重要 。 重要的是父亲对我的期望总是落空 , 我没有成功地做成一件事 , 让父亲心里妥帖 。 我就像一块盐碱地 , 只投入不产出 , 他的两次心血都都付诸东流 。 当时的父亲不知道 , 他的所有努力都没有白费 , 那些经历渲染了我生命的底色 。 学习让我了解世界 , 并成了我一生中每天坚持的习惯 。 学艺让我走出乡村的视野 , 以更大的视角从另一个侧面看待世界的不同 , 仰望城市的星空 , 吞吐云烟 , 并能将它们诉诸于文字而长久地回味缅怀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本文转自:文汇网1、设计用途不同或许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 卷纸和抽纸都能擦嘴吗?专家:一节卷纸和一张抽纸的细菌数量差距大概相当于一只手上的细
- |于文文卸任队长,愉快加入郑秀妍同盟,张俪自我安慰太好笑
- 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道:“中年以后的男人 家庭对男人的影响,是直接的,也是深远的
- 张爱玲笔下的一句话 新的开始,有一个必须的前提,与过去做一个了断
- 张贤亮的笔下有一句话 夫妻生活中,为什么有些男人总是感觉压力很大?
- 张天爱|真寄人篱下,张天爱小时候借住老师家,小心翼翼怕说错话
- 张靓颖|张靓颖与冯轲离婚4年:她单身与伤病抗争,他做称职的单亲爸爸
- 曾经我跟张华结婚的时候 其实兄弟姐妹之间,年长的帮助一下年幼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 本文转自:央视新闻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张汝佳 是一名预备警察 她的父亲张保国 是一名排爆警察...|父亲排爆时被烧成重伤,女儿长大后选择……
- |汪小菲张颖颖与晚晚夫妇同行,穿情侣鞋走爱的街道,网友:神仙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