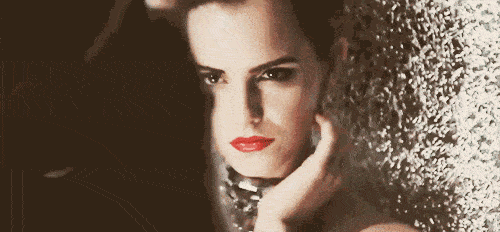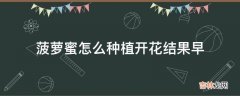3
这样似乎是由个体性差异所造成的相悖的爱情样态 , 其实指向的是最深处的关于“爱”与“欲望”的错位性理解——在很多人的理解中 , 爱与欲望是同一的 。 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中谈到了雅克·拉康的一个观点:“性并不使人成双成对 , 而是使之分离 。 ”“实在 , 却只是快感把您带向远处 , 远离他人 。 实在是自恋式的 , 其关系是想象的 。 ”“在性之中 , 最终 , 仍然只不过是以他人为媒介与自身发生关系 。 他人只是用来揭示实在的快感 。 ”换句话说 , 在由快感抑或欲望所催生的表象性的“共同体”中 , 两个“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关系是不存在的 , 其在本质上最终只是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 , 那个所谓的“对象”或“他者”不过是一个通向自我满足、自我完成、自我确证的“中介” 。 因此 , 在这样一种虚假的关系中 , 差异性是不存在的 , “两个人”是不存在的 , 只有“我”一个 , 这样一种绝对的同一性 , 也注定会坠入一种绝对的孤独 。
而“爱”则相反 。 “在爱之中 , 主体尝试着进入‘他者的存在’ 。 正是在爱之中 , 主体将超越自身 , 超越自恋 。 ”“在爱之中 , 相反 , 他者的媒介是为了他者自身 。 正是这一点 , 体现了爱的相遇:您跃入他者的处境 , 从而与他人共同生存 。 ”爱是一种真正的“关系” , 它超越了自我指涉的封闭性回路 , 而是朝向他者的 。 爱是“我”和“你”的相遇 , 是“我”面向“你”走去 , 踏入“你”的生命体验 , 对“你”的轻轻拥抱 。 一如巴迪欧指出:“爱总是朝向他人的存在 , 他人带着他(她)的全部存在 , 在我的生命中出现 , 我的生命于是就此暂时中断从而重新开始 。 ”在爱中 , “我”的世界不再是同一性的重复 , 而是藉由差异性的相遇孕生出一个新的世界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爱是具有某种本体论意义的 。
而立春和立冬对柳川目光的云泥之别恰好诠释了这样一种“欲”与“爱”的不可通约性 。 立春对于柳川 , 与其说是爱恋 , 不如说是情欲 。 阔别二十年后 , 立春最留恋的 , 依旧是柳川的肉身 。 他经由对柳川这样一个曼妙女子的带有情色意味的凝视 , 确证了自己尚未凋萎的男性力量 。 所谓的爱情 , 其本质上依旧是“自恋” 。
而立冬对柳川的爱 , 则走向了一种“真理性的建构” 。 他纯然地进入了柳川的存在 , 柳川的境遇 , 柳川的生活 , 而不是将柳川视作向自我复归的“媒介” 。 因此 , 即便在漫长的岁月中 , 柳川从未给予他回应 , 他也依旧安静地爱着她——在这个从差异性出发去体验着的世界中 , 爱是高于他自身的 , 那个唯一的“主体” 。 与其说他所朝圣的是柳川 , 不如说是绝对的爱本身 。 当她因为口音被小伙伴排挤而憎恨北京话 , 他戒掉了北京口音;当她被立春抛弃而意难平 , 他每天陪她去后海等立春;他录下了她第一次清唱的《Oh my love》;他为她学习了日语……在柳川同泡温泉时 , 立春轻佻地说出那句:“你看川儿越来越性感了” , 而他却温柔地问她:“阿川 , 你幸福么?”他“看见”了她 , 从此跃出了自身 , 只关切她的生命情状——最本真的爱 , 便是这样无关欲望 , 无关回馈 , 而与她(他)命运的自觉的羁绊 。
4
立冬也曾短暂地迷失于欲望之中——那次突破禁忌的触摸 , 却让他介怀与负疚了二十年 。 在柳川 , 立春鼓励他释放欲望:“川儿她挺随便的” , 但他最终 , 只是给了自己一耳光 。 这一耳光 , 是一种认命——他处处模仿哥哥 , 却始终和哥哥“有壁” , 那样的放浪终究不属于他;亦是一种抵抗——对于一个不爱自己的姑娘 , 一点世俗的情欲流淌都会构成一种侵犯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女性主义|我们如何讨论“女性权益”
- 恋爱|容易被男人“玩弄”感情的女人,往往有三个共性
- 女生若是想你了,会把这些话挂在嘴边
- 《玫瑰之战》:在职场中完胜情敌?你只需要学会这一招
- 秋天的风文|丁立梅我和几个孩子站在一片园子里 我和几个孩子站在一片园子里,感受秋天的风
- 人这一生,总有人在渡你
- 和你在一起|追女人的4个套路,一旦学会,她早晚会是你的人
- 大龄剩女|一线城市的“大龄剩女”,会越来越多
- 恋爱观|年轻人新型恋爱观上热搜:“长相身材无所谓,重要的是脑子”
- 蒋南孙|人这一生,总有人在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