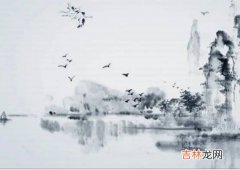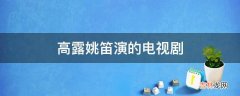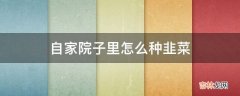回来后 , 戴锦华频繁出现在大众文化的战场 。 无论是媒体采访、公开演讲 , 还是文化活动 , 戴锦华始终保持着对于社会与文化动态的高度关注 。 她研究流行文化 , 虽然很多时候是本着敬业的精神 , 但她真切地希望从中理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 体会这一代人的爱与怕 。 她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那些无解的问题 , 分享20世纪的逻辑 , 青春的逻辑 , 革命的逻辑 , 虽然很多时候她收到的反馈是“老师 , 你别……”的提醒 , 和一种被她称之为无法化约的“代沟” 。
与此同时 , 21世纪以来全球经历的新一轮变迁 , 让戴锦华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修订此前逐渐沉淀形成的问题系 。 当然 , 其中也有一些不曾变过的问题 , 譬如“我们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召唤新的历史主体?”她认为 , 左翼思想者的工作始终围绕于此 , 也受困于此 。

本文图片
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 。
2021年10月 , 我们和戴锦华做了两次访谈 , 聊了将近六个小时 。 第一次访谈 , 我们从她的学思历程聊起 , 聊到她生命中的困惑 , 聊到她对于当下现实的诸多追问 , 贯穿其中的 , 仍是许多无解却重要的问题 。 譬如 , 当我们提及她如何理解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断裂 , 她坦言:“我们需要坦荡地承认 , 我们此前既有的知识和思考近乎完全失效 , 我们对于这个被疫情所改变的世界和疫情之后(如果有)的世界 , 很可能一无所知 。 ”
我们也聊到女性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 聊到我们各自与女性主义的连接 。 “事实上 , 我与某种内在的极度自卑 , 或者说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厌恶感搏斗了几十年 。 我毕生在学习一件事:接受自己和背负起自己 。 ”听到戴锦华在我面前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 , 我有点不知所措 。
第二次访谈很短 , 我问她:“你对这个世界的原点式相信是什么?”
她沉默了一阵子 , 忽然看向我说:“很早以前 , 我和一些朋友有过一次比较动感情的讨论 , 聊到对我们来说 , 什么是最具神圣感的所在?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 , 现在依然如此 , 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 ”

本文图片
电影《都灵之马》剧照 。
以下是新京报采访人员对戴锦华教授的专访 。
专访戴锦华
接受自己 , 并背负起自己
//
PART 1.
学思历程:危机与应对
1.1
我的学术自觉:
它必须与我的真实生命紧密相关
新京报:在过往的采访与文章中 , 你曾提及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困惑总会造成某种学术或思想的转型 , 而这些困惑又往往跟中国社会的转折有关 。 我们不如先从这几次困惑及转型开始说起吧 。 从今天回望过去40年的学思历程 , 你如何定位这几次转型?
戴锦华: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 我会有一点迟疑 , 原因可能在于“学术转型”这个词 。 直到今天 , 我这一生从开始时的不自觉 , 到后来的高度自觉状态 , 我的学术必须与我的真实生命、我的社会生存与我的社会关注紧密相关 。 这种相关度以及我用个人生命去面对与体验它的真诚度 , 对我来说是首位的 , 而学术评价系统反而要次要得多 , 我甚至不能或者说不想勉强自己去调整这种状态 。 所以你也可以说 , 我的学术不是为了学术生产而生产 , 而是我不处理它 , 我会不安 , 甚至夸张一点来说 , 我不处理它就难以让自己的生活继续推进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外婆拔“刀”,母女只剩命苦!记戴安娜这位同在宫里的亲戚!
- 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逝世25周年前夕,车祸豪车下落不明,车主要求“物归原主”
- 离婚一年后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起因竟是女王手写的离婚信?
- 一场完美的婚礼 干货分享,解锁婚戒佩戴的正确姿势!
- 戴安娜|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42岁董洁下地干农活,徒手捏虫子不戴手套!对比王艳差距就出来了
- 作者:黎荔从来不喜欢穿金戴银 童年时代的耳环
- 戴大爷的儿子戴伟早些年为了钱 父亲去世后,戴大爷把三十万存折全给了自己的侄儿
- |拉风!梅西夫妇约会共进晚餐,梅西戴百万百达翡丽鹦鹉螺,安妞拎香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