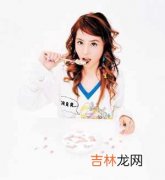本文图片
《乌托邦年代:1968-1969 , 纽约-巴黎-布拉格-纽约》 , [法]让·克劳德·卡里耶尔著 , 胡纾译 , 读库 | 新星出版社 , 2018年4月 。
第三条线索重要而偶然 。 我和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朋友共同开启了“广大第三世界”的访问考察和中国乡村调查 , 也参与这两个场域相关的社会行动 。 我几乎出席了每一届世界社会论坛 , 和包括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乔姆斯基等在内的左翼思想者的共同行动和讨论 。 这段时间中 , 我参与了全球千名妇女征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 , 作为中国协调人参与了一个中国基层妇女的网络的建立 , 到今天我还跟他们保持联系 , 仍在试图运行这一共享、互助的网络 。
与此相关的是新乡村建设运动 。 从运动开始构想和讨论到正式开启 , 我始终是参与者 。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志愿者 , 尽管我也参加组织工作 , 但我始终未能获得一种笃信或把握感 , 我仍然未能确认“我要什么”的问题 。 或者说我未能获得一个令自己确信的答案——20世纪的历史债务对我说来 , 依旧沉重而巨大 。 当然 , 我相信这是一次重要的社会试验 , 是众多年轻人的宝贵的另类选择 。 所以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 愿意充当“工具人” 。
直到最近 , 梳理世界电影现象时 , 我才发现自己确乎漏掉了这十年间登临影坛的一代导演 , 或者那十年我没有付出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追踪影坛的最新的动向 , 我当然会看电影、读小说——那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 但我的时间和热度则投注在上述三方面 。

本文图片
戴锦华在FIRST青年电影展 。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
新京报:我记得在你和吴琦的访谈文章《我们丧失了对当下世界的把握感(上/下)| 戴锦华专访》中 , 你将自己这十年的尝试归结为失败 。 为什么这么说?
戴锦华:就每一条线索的原初诉求来说 , 可以叫失败 。 但收获和意义却是在日后的岁月中逐渐显影的 。 在后革命与历史思考的层面上 , 收获是我不曾预期的 。 当我尝试以感受的方式重新叩访历史之时 , 我第一次获知或曰体认到了法国大革命胜利之后 , 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民众和反抗力量经历的低迷、失望与愤怒 。 和我想象中的胜利之后不同 , 可以体认到的是激变之后的创伤 , 社会的凝滞状态 。
最始料不及的收获 , 是对那些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读物 , 尤其是其中西方文论著作的再认识 。 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 , 艾克曼的《歌德谈艺录》 , 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流》等等——这些著作都是我们年轻时耳熟能详并且反复诵读的 , 而在此之前 ,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和历史之间的关联 。 当我重新进入这段历史时 , 才第一次意识到它们事实上充当了法国大革命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过程当中的某一种过渡或曰中间物 。 某种意义上 , 它们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预备期 。 这一发现 , 第一次令我真切地理解为什么20世纪的革命者经常经由文学走向革命 。 对我而言 , 这谈不上是对历史的发现 , 却是重要的历史体认 。 由此 , 历史对我展示出隐现中的线索 。
《艺术哲学》 , [法]伊波利特·丹纳著 , 傅雷译 , 安徽文艺出版社 , 1999年1月 。
对我来说 , 这构成了鼓舞和安慰(也许有阿Q之嫌?) 。 当我们茫然、感到无力和有限时 , 我们深知历史不取决于个人的愿望与意志 , 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大潮中 , 坚持做自己能做并且渴望做的事情 。 至于这些工作在历史中的意义 , 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 这给了我一种支撑 , 让我可以继续我感到疑虑的学术与思想工作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外婆拔“刀”,母女只剩命苦!记戴安娜这位同在宫里的亲戚!
- 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逝世25周年前夕,车祸豪车下落不明,车主要求“物归原主”
- 离婚一年后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起因竟是女王手写的离婚信?
- 一场完美的婚礼 干货分享,解锁婚戒佩戴的正确姿势!
- 戴安娜|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42岁董洁下地干农活,徒手捏虫子不戴手套!对比王艳差距就出来了
- 作者:黎荔从来不喜欢穿金戴银 童年时代的耳环
- 戴大爷的儿子戴伟早些年为了钱 父亲去世后,戴大爷把三十万存折全给了自己的侄儿
- |拉风!梅西夫妇约会共进晚餐,梅西戴百万百达翡丽鹦鹉螺,安妞拎香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