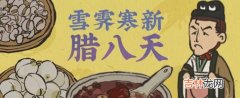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 , 在其小说《母亲》中 , 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 , 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 , 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 , 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 , 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 。
生命在他们眼中 , 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 , 活着 , 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 , 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 , 死去 , 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 , 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 , 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 。
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 , 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 , 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 , 除了让他们吃饱饭 , 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 。 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 , 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
最后 , 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 , 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 , 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 。 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 , 但在实际情况中 , 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 。 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 , 风景算不上太好 , 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 , 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 , 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 。
但近两年 , 不知哪里来的人 , 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 , 河流也被迫改道 , 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 , 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 , 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 。 事实上 , 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 , 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 , 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 , 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 , 农田被占 , 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 , 现在根本无法预料 , 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 。 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 , 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 , 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 , 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 , 作为家庭中的一员 , 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 , 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 , 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 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 , 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 , 他们的实际生活 , 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 。 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 , 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 , 又何以可能?
03
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 , 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 , 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 。 但每次回乡 , 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 。 尽管手头总是缺钱 , 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 , 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 , 哥哥从不失眠 , 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 。
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 , 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 , 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 。 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 , 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 , 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 , 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 , 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 。 而如何回馈家庭 , 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 , 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
冷静下来想想 , 关于对乡村的回馈 , 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 , 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 , 自古至今 , 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 。 我父母辈如此 , 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 , 这一点 , 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 。
我想起我的父母 , 半生以来 , 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 , 有一份公职 , 妈妈因为能干 , 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 , 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 , 几十年中 , 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一个女人最好的嫁妆就是一颗体贴温暖的心 婚姻进入瓶颈后,怎么熬过柴米油盐的无聊期?
- 离婚|“过完年了,咱们去离婚!”春节后离婚率飙升,现代人的婚姻咋啦
- 最近有位读者给我留言说:“中年女人真的很可悲 中年女人离婚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诉苦?
- 01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离婚的男人比离婚的女人更吃香 离异带着孩子的女人,真的适合你吗?
- 婚姻有时真的让人捉摸不透 这3种婚姻,最折磨人
- 01不管是明星夫妻还是寻常夫妻 男人出轨后,最后受伤的终究是女人
- 结婚|结婚前给女人的忠告:只承诺不行动的男人,不要轻易嫁
- 冯化成|人世间:周蓉这样自私的人,才有离开冯化成的底气
- 朋友在精,不在多,和值得交往的人共相处,和心里有你的人做朋友
-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为什么丁克夫妻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