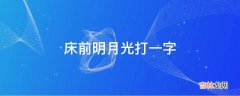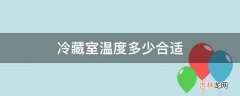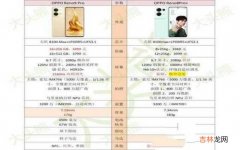有时放学回家 , 门被锁住 , 兄妹俩进不去屋 , 坐在家门口哭 。 朱大红回来 , 看见孩子们哭 , 她也跟着哭 。
这种时候 , 她总是格外想念陆中明 , 但又不敢跟孩子倾诉 , 怕惹得他们伤心 。 偶尔陆阳惹她生气 , 她才会吐出一句:“你没继承你爸爸的聪明 。 ”
陆阳和陆晴对父亲的记忆 , 全部来自于照片和母亲的只言片语 。 在陆阳保留的照片里 , 父亲的笑容总是舒展——有撑在摩托车上的 , 有站在油菜花田里的 , 还有和朱大红并肩坐在一起抱着孩子的 , 照片里母亲的脸上也有笑容 。
在朱大红的印象里 , 孩子们只知道父亲去世了 , 案件细节直到劳荣枝落网后才知道 。 但在孩子们的世界中 , 没有了父亲 , 本身就意味着不同 。
陆阳最怕开家长会 , 他不愿意回答爸爸为什么没有来 , 性格也越来越自卑 。 青春期时 , 也像其他孩子一样 , 有点叛逆 , 跟着调皮的同学拿了一把别人家门口晒的花生偷偷卖掉 , 被老师请了家长 。 朱大红从打工地赶到学校 , 走一路哭一路 ,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陆阳推着自行车跟在母亲身后 , “那一刻我感觉我特别错 , 一下子就成熟了 。 ”
从那之后 , 陆阳很少和母亲顶嘴 , 感到委屈时 , 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 。 他学会了跟自己和解 , “爸爸不在了 , 妈妈一个人不管多难也想把这个家撑起来 , 我得赶紧长大 , 照顾我妈妈 。 ”

本文图片
朱大红曾用来拉稻子的木板车 , 现在被搁置在墙角 。 新京报采访人员 左琳 摄
把家撑起来
要不是几个月前 , 朱大红把腿摔断 , 不得不在家休养 , 她还会在合肥没日没夜地做着那份宾馆保洁工作 。
她已经干了十几年 , 早中晚三班倒 , 旺季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 打扫三四十间客房 , 长期甩被子、换床单、刷马桶 , 她的肩膀、双腿和腰背时常疼痛 , 总是贴着膏药 。 即便气力耗尽 , 每月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块 。
为了加班方便 , 朱大红花一两百块钱在市区租了间民房 , 水泥墙壁光秃秃的 , 连陆阳也不大愿意去 , “天稍热 , 就像进了微波炉 , 透不过气来 。 ”
这样也比每天来回跑强多了 。 从村里到打工的地方将近20公里 , 朱大红要先骑电动车到公交站 , 她近两年才学会骑 , 车技还十分不熟练 , 正常不过20分钟的路程 , 她要花去近3倍的时间 。
早些年还没公交车的时候 , 路上要耗费更久 。 早上四五点钟 , 她就要从家出发 , 一路走到村口或镇上 , 再搭车穿过半座城市 , “每天早出晚归 , 一路哭着去合肥打工 。 ”
赶上农忙就更不得了 。
下班后 , 朱大红要立刻赶回村子 , 在门口点盏灯 , 一个人把白天晒好的稻子再翻一面 , 直至半夜 。 到了浇水的季节 , 她挨家挨户借机器抽水;该收获的时候 , 因为没有拖拉机 , 朱大红只好拉着木板车割稻子 , 两个孩子在后面推 , 至少要走两里路 , 万一碰到下雨 , 就只能任由稻子被淋湿发霉 。
“那些日子 , 天都是黑的 , 看不到亮 。 ”其实改嫁不是没可能 , 但她不愿意 。 “宁可我自己苦 , 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 不能让我的小孩成了孤儿 , 最后成了流浪儿 , 说不定走向社会成为什么败类 。 ”

本文图片
朱大红家里煤炉与煤气灶 , 墙壁已经被熏黑 。 新京报采访人员 左琳 摄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亲人|家庭中,有这么两类人,跟亲人窝里斗,可对“外姓人”特别好
- 二刷《沉香如屑》,才懂得“真是疯了”这4个字中,隐藏的3层含义
- 让女人动情,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情”
- “败夫”的女人的4个特征,男人一旦娶到,这一生就完了
- 为什么有些人,非要到了谈“彩礼”时,才分手?
- 本文转自:长江日报游客在东湖畔乘凉消暑。|东湖“亲水秘籍”大公开,这些“能人”如此玩水
- 恋爱|“恋爱3年,被家暴1次,10天后离开”:这场教科书式分手,值得一个热搜
- 社交|聪明人都开始过“低配生活,高配人生”了,你还在“奢侈成瘾”吗?
- 聪明人都开始过“低配生活,高配人生”了,你还在“奢侈成瘾”吗?
- 本文转自:光明网爱你孤身走暗巷 “叔叔救你,不敢哭!”为救2岁男孩,他毫不犹豫跳进了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