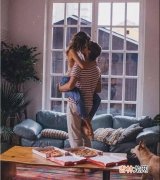另一类反应则在齐美尔那里得到了刻画 。 齐美尔同样认为现代人面对着一个充满了“流变、易逝性和不确定性”的生活世界 , 但在他看来 , 当人们的神经因不断的刺激而麻木和厌倦 , “冷漠”也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反应甚至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 在齐美尔那里 , 出于“冷漠”的需要 , 人际间的交往“是功能主义的 , 表面性的 , 非个性化的 。 ”在某种意义上 , “边界感”这一概念在当代话语中的兴起或许正与此相关——边界感旨在将社交限定在一个“浅尝辄止”的范围内 , 让人们以彬彬有礼的方式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 , 借以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 , 逃避相互间的“碰撞”可能带来的“震惊”和“恐慌” 。

本文图片
《现代性》 , 汪民安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
值得注意的是 , “社牛”或许也可溯源至齐美尔所指认的“冷漠” 。 如果说“边界感”还意味着将自身与“人群”的距离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 那么当人们在刺激下进一步“麻木”时 , 他们完全可能进展为对陌生的人群毫不在意 , 由此也无需保持距离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 “社牛”们可以在繁华的商圈或校园操场公然唱歌热舞 , 还可以在海底捞这种对“社恐”很不友好的店铺中跟店员热情互动甚至“反杀”后者……这一切似乎意味着曾让本雅明感到“惊恐”的人群似乎已无法激起社牛心中的半点波澜 , 以至于他们无需保持边界就能让自己如鱼得水 。 在某些人看来 , 这是一种对现代性生活十分有用的品质 ,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 , 这种做法让“边界”受到威胁 , 进而类似于一种哗众取宠的“社交恐怖分子”行为 。
如果说“边界感”和“社牛”都肇始于对人群所带来的“震惊”的防御 , 那么最后一种反应则力图以积极的方式“控制”本不可控的人群 , 这也就是麦金太尔所说的“操纵性”的态度 。 操纵性的态度旨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态度 , 并以此转变他人的情感与态度 。 ”如若对他人情感的转变和操纵得以可能 , 那么原本难以捉摸 , 进而带来无边压力的他人也就不再可怕 。 事实上 , 《卫报》也对这样的态度有所洞察 。 在其作者看来 , 卡耐基的代表作《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对此有充分体现 。 这本书的标题就表明:“朋友不是用来交的 , 而是用来‘赢得’的 , 交朋友的唯一目的就是让自己能为所欲为 。 ”
也正是随着这种观念的出现 , “有毒的友谊”开始被人们所警惕 。 在“有毒的友谊”中 , 你的朋友“不倾听你的问题 , 不理解你的情感 , 总想谈论自己 , 不因你的成功而快乐……”显然 , 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操纵性”的态度 。 在这种关系中 , “你”仅仅是被对方影响和“赢得”的对象 。
简言之 , 现代背景下的种种社交体验大多肇始于面对匿名人群的“震惊”——这种感受与“社恐”心态关联密切 。 为了面对“震惊” , “边界感”和“社牛”虽看似采取了相反的方式 , 但实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旨在保持一种对人群漠不关心的态度 , 以免在刺激中精疲力竭 。 而“操纵性”的态度则积极地介入人群 , 并力图“赢得”并“影响”自己的朋友 。 然而 , 也正是这种态度令友谊变得可疑 。 事实上 , 这几种共同的体验背后都有一抹共同的底色——那就是所谓的“习得性孤独”——人们与“人群”的关系要么是格格不入的 , 要么停留在外在性的层面上 , 而这也令为现代性体验所支配的社交成为了问题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异性相处,两个人“感情走到尽头”的3个信号
- |英王小弟介绍索菲新头衔“公爵夫人”,有点不好意思,跟哈梅不同
- |闲聊错过4岁放学娃 妈妈求助民警后“虚惊一场”
- |仙侠剧最“惨”女主?从开头一直“惨”到大结局
- |换尿布、冲奶粉,出警民警秒变“宝妈”
- |凯特王妃包头巾太美,完胜“恰巧”露面的梅根,和男士握手时遇尴尬
- |《我们的日子》翻版“凤凰男”?王明中追求白富美,理由却很奇葩!
- |“王室四人组”缺席莉莉贝特受洗仪式,小公主头衔获国王爷爷默许
- |个人成长心理咨询:“不想结婚的我,成为了妈妈心病的症结”
- |心理学:一个人没什么朋友,也“不爱合群”,这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