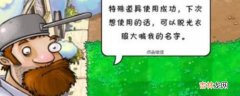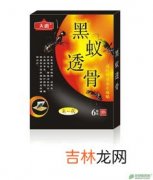那段日子就像一个黑洞 。 最可怕的并非怨天尤人式的沉坠(“为什么偏偏是我?!”) , 而是你在沉坠中还会欲罢不能地自我否定和质疑:是不是你的问题?你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种结果?你的女性身份是否已被剥夺?你怎会把自己搞得如此偏执而脆弱?……
我和铭基一直对孩子不感兴趣 , 严格避孕以免节外生枝 , 直到三十岁后我才第一次隐隐感受到了生物钟的召唤 , 谁知那竟是一连串噩梦的开端 。
为什么你变得如此执着于生育?我不断地质问自己 , 你究竟是真的渴望一个孩子 , 还是只为争一口气 , 想证明你有生育的能力?这对你的伴侣是否公平?你们的关系会不会因此改变?你是否比他更有资格做出生育的决定?你的“自由意志”又是否真的自由?并不是每次饥饿都会被填饱 , 每个欲望都应该被满足 , 如果你注定无法得到你缺少的东西 , 这种盲目的追逐是否仍有意义?你要到何时才能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事?这又将如何影响你的命运与自我认知?……
如果真能崩溃就好了 , 我常常想 , 尖叫 , 大哭 , 向人倾诉 , 尽情宣泄自己的痛苦 。 可正如许多与我境遇相似的女性一样 , 我们的内心充斥着永远不会变成闪电的雷霆 。 记得患葡萄胎住院时 , 如果不是因为铭基一人无法全程照护 , 我甚至不想告诉我的父母 。 我每天躺在病床上配合治疗 , 朝所有人微笑 , 一脸平静地看着英剧《唐顿庄园》 , 而那些疯狂的念头已经在大脑里绕了地球三圈 。
为什么你宁愿选择独自消化?另一个我冷冷地发问 , 你担心在家人朋友面前失态吗?你认为把痛苦传递给别人是一种暴力吗?还是说 , 不育的羞辱比不育本身更为痛苦呢?你又为什么会觉得这是种羞辱?你明知将女性生理机能禁忌化和耻感化的社会文化是如此不公与荒谬 , 为什么还要沦为它的同谋?
这一切都发生在2014年之前 , 距离国内“女性主义元年”的到来还有很长的时间 。 那时公共舆论场中鲜有对女性意识和生育议题的探讨与价值论争 , 甚至连女性的身体经验(月经、怀孕、堕胎、生产、妇科病、性生活等等)都很少被表述和关注 。 彼时最受追捧的一类女性形象是精致时尚的全能型“辣妈”——超越了“黄脸婆”和“女强人”的完美女性化身 ,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 以钢铁般的意志维持身材和容貌 , 产后第二天小腹就自动消失 , 白天上市敲钟晚上辅导功课 , 优雅得体地培养出同样优雅得体的孩子……
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下 , 对于一个相信自己能够拥有一切的现代女性来说 , 生育也许是一个选项 , 但更多地被视为自我实现的必经之路——或早或晚 , 但招之即来 。 你几乎不会想到它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 而当“多次胎停”、“反复流产”、“不孕不育”的判决如铁幕般落下 , 你会感到自己被驱逐出了主流大道 , 变成孤魂野鬼游离在禁忌之地 。
但痛苦也是一种契机 , 它会发出一连串的追问 , 令你反思某种不假思索的理所当然 , 让你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道路 。 那时的我尚无能力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语言来分析自我 , 但如今回溯起来 , 我个人女性意识真正的觉醒无疑就发生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 , 仿佛所有曾经被故意忽略和挤压到潜意识里的感受都开始融会贯通——尽管并非铿锵有力的选择 , 而更像是无可逃避的命运 。
显然 , 我只是在以后见之明整合当时那些碎片化的思考 , 就像在地震之后清理心中的废墟 。 无尽的追问带来无尽的困惑 , 却并没有打消我继续尝试的决心——也许出于愚蠢的自尊 , 也许发自生物性的本能 , 也许只是想要对抗命运 , 也许人之为人就是会有暧昧芜杂的情绪 。 我只知道我痛恨那种逆来顺受的被动感 , 仿佛自己是一件任人摆布的物品 。 主动出击意味着寻找新的解法 , 新的解法则需要新的信息 。 于是我转向网络搜集信息 , 一头扎进少数群体抱团取暖的秘密领地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一个多月的假期 人这一辈子,有多少次别离,也许,别离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 生命中的每一刻 生命中的每一刻,都不是为了纠缠着我们
- 内心强大的人从本质上来说 内心强大的人从本质上来说,做最好的自己是一种和自我的连接
- 九言|得失都是考验,全在自我取舍
- 爱自己 九言 | 得失都是考验,全在自我取舍。
- 为了赶走空虚感 空虚是一种心灵的空虚感
- 彼得·杜拉克思想的三大标签,“自我控制”是核心
- 恋爱中的男男女女 人到中年就会明白,做自己想做的事,别再为了小事委屈自己
- 我们每个人都难免会为了生活或者工作中的一些小事而烦恼 心眼小的人,总喜欢对别人说的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细细的揣摩
- 人在职场,具备三种核心的价值,才能不断自我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