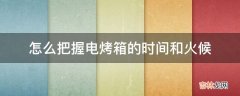|刘清平|康德感性任意意志观的悖论解析( 六 )
其实 , 只要我们恪守康德有关人类心理三种机能的严格区分 , 牢记是与应当的界限而不随意穿越 , 同时再引入康德倡导的“人是目的”的良善意志 , 像这样普通的日常行为既不神秘 , 也很容易解释:某人由于种种经验性先行因果链条所造成的生活方式 , 连同他因此形成的涉及人生价值理念的理知品格一起 , 会在某种氛围中引发他生出“想要说谎”的念头(自由意志) , 因为他觉得说谎虽然会伤害其他人 , 却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 。 结果 , 在“人是目的”这种规范性自由意志(亦即康德说的“良善意志” , 而不是他说的“理知品格”)未能发挥主导效应的情况下 , 此人就在“说谎谋利”的规范性自由意志(亦即康德说的“恶意”)的驱动下从事了说谎行为 。 有鉴于此 , 倘若我们站在“人是目的”或“不坑害人”的规范性立场上 , 就会因此谴责他这种为了自己趋善避恶却不惜让其他人缺失善而遭受恶的卑劣行径 , 在承认并批评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的同时 , 要求他对自己基于自由意志从事的这个行为及其后果承担自主责任——尽管此人也许会站在“为了利己怎样做都可以”的规范性立场上 , 认为这个行为是在实现自己从心所欲的“正当自由”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 进一步看 , 假定此人事前在理性上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说谎或这种说谎会伤害其他人 , 我们也会相应地减轻对他的道德谴责 , 而不会将他的行为张冠李戴地完全归咎于理知品格的失职 , 却忘记了他自己“想要这样做”的自由意志这个作为原初动力的罪魁祸首 。
现在我们就能看出 , 康德特别强调的“任意意志”与“良善意志”的区分 , 和认知维度上的“感性”与“理性”之别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 倒不如说归根结底在于它们在欲求维度上指向的质料性内容(目标或对象):你在基于自由意志从事各种人际行为的时候 , 是不是能够严格恪守“人是目的”的伦理底线 , 时刻保持“不坑害人”的道德良心?至于你究竟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 也根本不取决于你的“理知品格”有多么高 , 而是仅仅取决于你是不是怀有“把所有人当人看”的规范性态度 。 所以 ,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下面这类对比鲜明的反差现象:某位现代的高智商者凭借理性的计算精心策划了一场大骗局 , 而许多古代的质朴农民虽然没有多少思辨的知识 , 却始终拒绝去做坑人害人的“亏心事” 。 就此而言 , 康德单凭感性与理性的认知性标准区分欲求性的任意意志与良善意志 , 无疑是一种会在实践中产生严重误导的理论扭曲 , 有碍于我们在实然性层面上深入揭示那些仅仅把人当成工具的道德邪恶行为的产生根源 , 尤其是引导我们误以为它们只是来自所谓“理知品格”的高低水平 。
综上所述 , 由于不仅穿越了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认知与意志之间的严格界限 , 而且还恪守将自由与必然直接对立的二元架构 , 康德在从理性主义的规范性立场出发 , 凭借认知性标准把自由意志的价值诉求强行区分成感性任意意志和理性良善意志的过程中 , 不仅出现了混淆概念、自相矛盾、跳跃式推理等逻辑上的混乱错谬 , 而且还在理论上遮蔽了自由意志的实然性本来面目 , 尤其是将感性任意意志只能趋善避恶的内在逻辑扭曲成了可善可恶的随机偶然 , 将人们对于自己从事的自决选择所承担的自主责任仅仅归咎于所谓的“理知品格”而不是作为原初动力的自由意志 , 结果对一个普通的日常任意行为也难以做出有说服力的清晰解释 。 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缘故 , 本来在他的哲学大厦中扮演着联结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拱顶石”角色的“自由”概念 , 最终像他自己在试图论证自由存在的正题里反讽性地承认的那样 , 构成了一块“哲学上的真正绊脚石” , 把他引入了一座他自己精心设计却又永远走不出来的理论迷宫 。 就此而言 , 揭示康德哲学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的深度悖论 , 纠正其中的种种混乱错谬 , 对于我们今天解开绵延了两千余年之久的自由意志之谜 , 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姐妹花|电视剧《女人万岁》杀青,殷桃、刘以豪等领衔主演
- 本文转自:速新闻寄件人:刘运刚年龄:47岁职业:社区干部(速新闻记者 徐其崇)“这张明信...|明信片上的“微心愿”?丨愿做“三重父母”的好“儿子
- 本文转自:九派新闻去年“河北邢台男孩刘学州寻亲”一事曾引网友广泛关注。|河北寻亲男孩刘学州发文称不会起诉亲生父母:不会原谅他们,只是弟弟妹
- 本文转自:合肥交通广播前段时间孙海洋寻子成功后 邢台寻亲男孩刘学州疑被生母拉黑,发声称再遭亲生父母遗弃
- 刘航 丈夫出轨,情人欲看原配笑话却反被给500块服务费:我还得谢谢你
- 刘之冰|刘之冰继女奚望:结婚前继父心疼的睡不着,婚礼上泪洒现场
- 刘学州|刘学州公开与妈妈聊天记录,惨遭对方拉黑,无奈向爸爸发出三问
- 刘彻|你不知道,女人一旦动情,表现无法隐藏
- |“刘亦菲彩礼20w?”普信男聊天截图把我看傻了!网友:简直离了个大谱!
- 殷桃 殷桃的身材,梅婷的黑眼圈,都比不上刘涛的综艺脸,让人倍感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