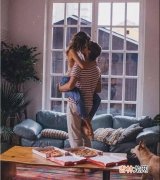曾奇峰老师说过,人活着是靠四个轮驱动的:力比多、攻击性、自恋和关系 。
身份的丧失,比如降级或撤职,会让自恋严重受挫,并间接的影响到关系,从更深层的角度讲,如果一个人有着病理性的自恋,他就会认为自己是完美的,不可能犯错,也不允许自己受挫,这样的人会用“婴儿式的暴怒”(自恋型暴怒)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
在近几年的新闻中,类似案例屡见不鲜 。
比如:一个31岁的青年赵某,因嫌弃排在一个前排的女孩取款太慢,产生争执,后来用兜里的折叠刀将其刺死 。

文章插图
何某带着自己的女友吃饭期间,遇到几个熟人过来敬酒,当其回敬时被对方拒绝,何某顿觉没有面子,双方因此发生口角,后来拔刀相向,捅死两人后改名换姓,在流窜期间被抓捕归案 。
恰当的自恋是好的,能让人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处在一个适合的位置 。在上面的事件中,当事人的愤怒和承受的“挫折”不成正比,正常的愤怒在达到目标后,就会消失,或者和当下的情景相匹配,比如:嫌弃前面取款太慢,在内心抱怨几句,或者敬酒被拒绝后有些不满情绪,但不至于杀人 。
婴儿式的暴怒则想要完全摧毁让他受挫的人或事,甚至摧毁后还不“解恨” 。
校园霸凌的施暴者,部分人的自恋程度趋近与病理性这一端 。
反观学校的管理者的自恋,虽然没有达到病理性的标准,但发生了这种事件,第一时间的行为也是掩盖和否认,而不是解决问题,这也反应出了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自恋,要付出多少代价 。
因为真相比谎言更让他们害怕,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管理的学校能出现这种情况,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疏忽和错误,通过否认来隔离自己的羞耻与愧疚 。
和这些校长类似,部分被性侵儿童的家长,也持有这种心理,尤其在农村地区,女童被骚扰传出去后,让家长很没有“面子”,孩子长大后也会被“吐沫星子淹死”,本来就受伤的孩子,被照料者在背后又狠狠地插了一刀 。
3.
如何改变?
可以参考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设置一些符合人性的规则 。
比如,设置举报霸凌事件的渠道,班主任或校长发现类似的行为,需要第一时间汇报,说明情况 。如果是被家长或其他人发现举报,作为校长和老师需要付出相应的严重代价 。

文章插图
发现霸凌事件后,成立调查小组,对施暴者直接惩罚,从口头警告到开除学籍,甚至是刑事责任,他们的父母会收到罚单,并规定重新对孩子进行教育,下次如果再犯,惩罚将加倍 。
这样的规则可以逆转博弈,在外在制度上,建立一个预防霸凌的流畅的机制,让超我重新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 。
我国现有的机制是,事情曝光以后在处罚,对预防霸凌和儿童性侵的过程没有监督,往往以“他还是个孩子”的借口模糊过去 。这句话作为施暴者的家长,可以掩盖他们的羞愧和自责,不必面对教育失败的自恋挫败,也可以逃避惩罚 。
这些“霸凌者”往往存在相似的心理防御机制,被“霸凌者”也是如此 。
比如,有的孩子仅仅因为同学在骑自行车时,超过了他,就进行殴打 。这要就要考虑自恋的问题 。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好斗”的学生,他父亲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来访者察觉不到对爸爸的愤怒,却在学校经常因琐事殴打同学,这就要考虑“与攻击者认同”这样的心理防御 。
按照他的话说:“我不打倒他,他就要打我,要对着头狠狠的打” 。来访者的父亲在家里就经常扇他嘴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