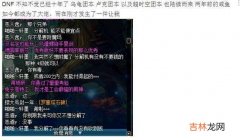本文图片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
另一项来自我国的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结论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佟新与王雅静曾在《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的性别比较》一文中 , 以武汉市和乌鲁木齐市为研究样本 , 搜集两市居民的基础出行数据指出 , 两性出行方式存在明显差异 。 女性更倾向于步行与公交 , 男性选择自驾或出租车的比例更高一些 。 而在出行目的上 , 女性的工作出行低于男性 , 与家务相关的出行活动则高于男性 。
尽管如此 , 在常见的城市交通规划中 , 必要出行(compulsory mobility)指的就是以就业和教育为目的的出行 , 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则经常被设计成为一种非必要 。 于是 , 清扫积雪的范围优先考虑的是机动车道 , 而非女性出行通常选择的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 。 城市道路规划也总是偏重汽车甚于行人 , 这才有了上述寸步难行的出行体验 。
不便之外 , 还有层层不安 。 在《看不见的女性》中 , 作者还提到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现象:女性在公共场所常常感到害怕 。 她们受到惊吓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 。 但是 , 官方统计女性所遭遇的暴力程度明显与她们的恐惧情绪不匹配 。 这一悖论甚至已经引出这样的结论——女性对犯罪的恐惧是非理性的 。

本文图片
美剧《闪亮女孩》剧照 。
这在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公共安全新闻里可见一斑 。 每当讨论涉及性别维度 , 不少人便会摆出理中客的姿态 , 认为公共空间的暴力问题并不存在性别差异 , 男性同样会遭到暴力威胁 , 甚至还会举出相关统计数据作为例证 。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 , 当我们提到不安时 , 这层不安并不单是由新闻报道的曝光度或统计数据中的数字所构成 , 它来自于实际的生活经验——在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发生前 , 女性每天都要面对令人感到不适的男性行为 。 小到被不怀好意地上下盯视、被莫名其妙搭讪并追讨微信 , 大到在拥挤的公车上被故意身体擦蹭、到站之后被尾随……这些行为无法被统计为明确的犯罪 , 但它们构成了一张以恐惧值为度量标准的城市心理地图 。
在上文提及的佟新与王雅静的研究中 , 当女性被问及出行安全挫折的经历时 , “有24.6%的武汉女性受访者和19.3%的乌鲁木齐市女性受访者分别报告了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过程中遭遇过的88例和62例性骚扰 , 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车内 , 也有发生在车站、地下通道和街道的多个案例 。 男性陈述有性骚扰遭遇的比例为0 。 男性在回答此问题时多噗嗤一笑 , 不以为然 。 ”
而当公共空间的性骚扰发生时 , 不仅存在漏报 , 还存在缺少上报程序的问题 。 “关于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时该如何应对 , 全世界都缺乏明确的指引信息(但对于可疑包裹 , 大多数官方部门似乎都设置了清晰的标识 , 告诉人们发现时该如何处置) 。 然而 , 有时缺少标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恰当的程序 。 ” 佩雷斯在书中说道 。

本文图片
美剧《闪亮女孩》剧照 。
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 , 如果女性在出行的人身安全方面存在更高风险 , 会发生什么?无论是在《看不见的女性》中所收录的研究数据 , 还是国内的相关研究 , 它们无一例外地表明 , 这一状况导致了女性对出行时间和出行范围的自我控制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婚姻|和朋友聊天,忽然聊到门当户对的感情比较稳定,你认为呢?
- 狮子座|和狮子座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 塔罗牌|塔罗:选择嫁给合适的人,婚后生活是将就还是会一直幸福下去?
- 孩子|总觉得自己是最倒霉的,这是在给自己埋“祸根”!
- 1.|搞笑段子:我鼓足勇气给我心仪的女生表白的事
- |《张卫国的夏天》还是太短了,仓促间,所有的前菜都成了摆设!
- 父母|父母,都是无师自通的PUA高手
- 情商|高情商女人的这些特点,总能让男人思念入骨
- 人性|总有一天你会彻底醒悟,人性,终究会是压垮老实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 相遇的地方|我们相遇的地方,细流如同青春时期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