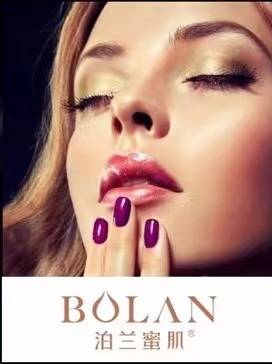|陆晔:“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女性学者访谈( 五 )
第一 , 对于公众而言 , 人们还看新闻 , 但是不再关心这条新闻是由哪家媒体生产的了 。 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 , 对消息来源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 比如我是读报的、我是看电视的、我是听广播的 , 我看的是中央电视台还是上海电视台 。 今天我们所有重大消息的来源都是社交平台 。 大部分人不是注意力分散 , 而是接收渠道改变了 , 人们看的内容可能依然是中央电视台、财新生产的 , 但他们不知道 , 他们只依赖于聚合式新闻平台所提供的内容 , 或是社交媒体上由周围的人对他造成的影响;
第二 , 从社会生活来说 , 在过去 , 个人的公共表达非常受限 , 无论是信息还是意见 , 只能通过几个有限的渠道 , 但今天不是了 , 抖音、快手等平台为每个人提供了表达渠道 。
面对这种传播环境的变化 , 我个人觉得对于传统机构媒体新闻编辑部的研究 , 在理论上难以再有突破 。 2016年我所发表的“液态的新闻业”和2018年发表的“媒介融合和协作式新闻策展”对我个人而言在理论方面几乎是到头了 。
所谓“液态新闻业” , 就是指整个新闻行业和社会状态已经改变 。 这一方面体现在新闻生产者的“液态”:新闻不再由一个固定机构所控制 , 在某个特殊节点上 , 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从业者 。 在流动的现代性中 , “液态”可能就是常态 。
同时我们发现 , 公共知识的生产现在可能出现在今日头条等聚合式新闻网站 , 或抖音快手这类短视频平台上 。 所以我觉得研究对象的转变是自然的 , 但这依然属于媒介社会学的范畴 , 我依然关注社会公共生活 , 依然关注信息流动和知识生产如何与公共生活发生关联 。
迄今为止 , 对于这种新的传播样态 , 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系统性的研究 。 这种新的传播样态 , 是多中心的、去中心化的、低门槛的 。 过去影像生产的门槛是很高的 , 但在今天 , 有那么多短视频剪辑软件可以选择 , 帮助你生产、剪辑视频 。 这到底给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哪些变革?我认为这方面的经验研究还远远不够 。
新京报:媒介社会学所身处的学科环境 , 以及它所面对的新闻生产业态都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之中 。 作为一门学科 , 它本身不变、或者说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
陆晔:不是说媒介社会学本身不变 , 而是关注社会的理论视角中有一个要素是不变的 , 即“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 。 落到具体的部分 , 就是所谓的客观真实、主观真实和媒介真实的关系 。 这样一种关注本身 , 是有它的一贯性的 , 人类认识外部世界 , 然后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反观我们自己 , 最后达成社会的连接 。 但在不同的理论路径之下 , 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
如果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 , 媒介社会学中有大量的讨论是把媒介和媒体技术看作社会的一种构造 , 先有了社会然后才有媒介技术在其中运作 , 社会是一个人一样的有机体;但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 , 就不是这样 。 它不把社会看成是外在于人的 , 只有人类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才是有意义并值得讨论的;而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 , 它关心的是社会是如何通过传媒 , 来建构起一种知识生产或文化 。
媒介社会学没有统一的定义 , 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理论来源 , 但是我觉得它最核心的部分——如果套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它关心的依然是“社会”和公共性的问题 。
新京报:但是所谓“公共性”又该如何判定?例如近期兴起的“公共艺术” , 和新闻传播之间也有大量的共同之处 , “公共性”的界线似乎是模糊的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林庆昆|《完美伴侣》“离婚了,我就没有家了!”林庆坤为何是这个反应?
- 真正的友情,从不喧哗
- 怎么放下一个很爱的人,如果你还没放下,不妨也可以看看
- “抠门9年”攒下两套房,真正的人间清醒是这样吗?
- 小熊与白生文字中一样的句子:花自向阳开人终向前走,是巧合吗?
- 爱上你 如何让女人爱上你?这个“稀缺能力”,普通男人要学会
- 备胎 “我有备胎,等玩够再嫁也不迟”女人自信过头,想嫁才知已成笑话
- 渣男 《2022年渣男语录合集》:“既不成全你,也不放过你”
- 过年 “你媳妇回娘家过年,咱家20来口人的年夜饭谁做”“我没媳妇了”
- “草包”领导一上任,就喜欢大肆做这3件事,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