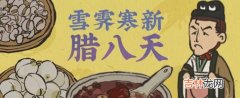同时 , 借助95世妇会的召开中国的性别研究经历了一次快速的学科化过程 , 女性议题被组织在女性学、女性研究、妇女史的学科和项目之中 , 因此而获得易于辨识的显影 。
如果说 , 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 , 中国妇女的性别渐次成为某种社会文化与自觉 , 女性文学因此获得了鲜明及可辨识的性别维度与差异性特征 , 那么 , 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与权利却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中经历着或快或缓的坠落 。 多少有些反讽的是 , 女性整体的社会生存状态与女性的性别意识及自觉再度朝相反方向背离 。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 戴锦华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年6月 。
我个人不认同女性书写经历整体性失落的结论 。 尤其是当我们将以网络为介质的女性书写纳入观察视野的话 。 只是我们必须再度提出那个句套子:当我们谈论女性文学时 , 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个人倒是趣味盎然地瞩目于以网络为介质的女性书写及多种文化衍生物所呈现出的我称之为“性别混响”的文化表征与现象 , 关注为新媒介改变的社会生产方式与劳动力组织形态如何在强化本质化的性别秩序的同时 , 令性别演化为某种cosplay/角色扮演式的存在 。 变化正在发生 , 尽管与我们曾经的预期不甚相符 。
3.4
娜拉与花木兰的困境:
我们如何想象多元的女性文化模板?
新京报:相较于当时 , 今天的“女性写作”或者更广泛的女性创作处于怎样的发展状态?
戴锦华:到现在为止 , 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生产出一种新的性别文化的模板 , 我们的突围继续遭遇着更多重的陷落 。 表象意义上的变化无法令我感到心安 。 因为我期待的 , 是社会平等的实践 , 是差异的尊重 , 而并非女性为主体或主导下的对父权、男权逻辑的复制 。 所以我无法简单认同所谓“大女主”式的流行文本 , 其基本特征是一个强悍的、掌控的、统治或驾驭的女性角色 , 而不曾展示其性别身份与生命经验如何内在地改变了掌控的逻辑 。 强悍的仍然是父权的逻辑 。 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我们曾把这类角色称为“代行父权之母” 。
我同样无法简单地以女性欲望的正义性之名 , 认同将男性形象、身体置于凝视/物化之间的“变化” 。 反转了的 , 只是性别身份间的位置 , 而非将人异化、物化的男权暴力逻辑 。

本文图片
电影《一代宗师》剧照 。
新京报:前段时间(编者注:采访时间为2021年10月) , 《人物》的一篇文章《平原上的娜拉》引发舆论热议 。 这篇文章回访了上世纪80年代《半边天》节目中一位叫作刘小样的女性 。 在讨论这篇文章时 , 大家反复提及的是刘小样作为“娜拉”这一现代女性形象在当时的显影 。 同时 , 借由刘小样的经历 , 我们也在反思今天女性的现实境况 。 我很好奇 , 你看完这篇文章的感受是什么?你如何看待“刘小样”的故事以及“娜拉出走”的镜中之意?
戴锦华 :我阅读过这篇文章 , 也被深深地触动 。 但阅读中会感到某种隐隐的疑惑 。 我感到从昔日的《半边天》对于刘小样的理解和解释到《平原上的娜拉》的写作 , 我们共同分享了一种认知 , 即 , 刘小样是一个被困在了乡村、传统文化、旧式亲属关系之中的女性 。 这或许可以解释她在乡村社会、婚姻家庭中的经历的不安、躁动 , 却难于解释她富有才情的写作能力 , 以及她以如此富于表现力的文字所传达的、精微细腻的内心悸动 。 换言之 , 我们先在的、也许未经反身的逻辑仍是现代性范式 , 一个现代社会妇女解放的路径 。 因此我们会给出“娜拉”的命名——尽管那是一个150年前的挪威故事 , 我们会给出一个娜拉出走的解决方案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外婆拔“刀”,母女只剩命苦!记戴安娜这位同在宫里的亲戚!
- 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逝世25周年前夕,车祸豪车下落不明,车主要求“物归原主”
- 离婚一年后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起因竟是女王手写的离婚信?
- 一场完美的婚礼 干货分享,解锁婚戒佩戴的正确姿势!
- 戴安娜|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42岁董洁下地干农活,徒手捏虫子不戴手套!对比王艳差距就出来了
- 作者:黎荔从来不喜欢穿金戴银 童年时代的耳环
- 戴大爷的儿子戴伟早些年为了钱 父亲去世后,戴大爷把三十万存折全给了自己的侄儿
- |拉风!梅西夫妇约会共进晚餐,梅西戴百万百达翡丽鹦鹉螺,安妞拎香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