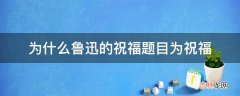《马克思的幽灵》英文版书封 。
PART 3.
性别议题:女性主义与文化困境
3.1
我仍然与我的自卑 ,
做着持久的搏斗
新京报: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 , 你是第一个在中国谈女性主义文学的学者 , 也是最早在北京大学开设女性文学课程的老师 。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 , 开启了这些工作?
戴锦华:你提到上世纪80年代末 , 我想起当时我和一个女性朋友的对话 。 她说:“我很惊讶 , 你会觉得自己和女性主义的连接是天然的 。 对我来说 , 这不是天然的 , 我必须要想一想自己与女性主义的关系 。 ”
我最早遇到的国外女性主义理论 , 都是经由断篇残简 。 但这些偶遇 , 不同于与其他理论相遇 , 它直接成为对个人生命的解惑 。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 我遇到过的深刻困惑与窘境 , 比如说身高 , 比如说是否像女人 , 如何做女人 , 等等 , 那曾是深深的困扰 , 是成长岁月无法排遣的烦恼与自疑 。 女性主义理论对我的最大助益 , 是让我明确地知晓 ,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 说得更朴素些:这不是我的错 。 因此 , 那与其说是一种理论的习得 , 不如说是我生命中一次可贵的相遇 。
因此 , 我直觉地选择女作家研究作为我的课题 , 偶然地与孟悦共同撰写了据说是国内第一本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专著《浮出历史地表》 。 也是那个时候我明确地意识到 , 也开始自称女性主义者 。
《浮出历史地表》 , 孟悦/戴锦华著 , 培文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年5月 。
新京报:所以是在那个时候 , 你有了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
戴锦华:应该说是获得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身高这件事 。 我记得你也曾提到过身高对于自我认知的影响 , 后来你是如何与它和解的?
戴锦华: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和解 , 而是一个持续的抗争 。 事实上 , 我与某种内在的极度自卑 , 或者说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厌恶感搏斗了几十年 。 也讲过很多次了 , 现在我很少提及与我自己相关的这部分事实 。 因为它间或被指认为某种“凡尔赛”——炫耀或造作 。 (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定我张扬、自信 , 在某些人看来 , 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本身便是某种侵犯性的姿态 。
在我自己的国际旅行中 , 遇到过许多引为知交的女性主义学者 , 其中不乏国际明星学者 , 我始料未及地发现 , 类似的隐痛和隐秘竟然是我们的共同经验 。
新京报:到了今天 , 你仍然在和这种不自信搏斗吗?
戴锦华:大约经历过四十大惑之后 , 我多少战胜了这一点 , 至少是治愈了关于自己的心理病态 。 从这种意义上 , 我毕生在学习一件事:接受自己和背负起自己 。
新京报:刚才提到身高这件事 , 我之前很诧异于身高带给你的焦虑 。 因为对我来说 , 我一直在和长得不高这件事做心理斗争 。 每一次要在公开场合说话 , 我都会因为自己的身高感到自卑 , 甚至还被人问过为什么不穿高跟鞋?
戴锦华:如果你问我 , 如何应对被人劝诫穿高跟鞋的问题 , 我会说 , 下一次再遇到 , 你回之以嫣然一笑——一个简单的个人主义回应 , 我的事情与你无关 。 同时 , 也不否定对方建议中可能有善意的初衷 。
新京报:我有时候会赌气地想 , 是不是随着年纪增长 , 女性被凝视与被审视的概率就会小一些?
戴锦华:我觉得很多时候 , 我们也在想象或内化来自男性的审视 。 什么时候你不再去想象和关注类似审视 , 便会赢得一个自我解放的时刻 。
对我自己来说 , 我一直感受着的是自我的审视 。 当然 , 这种结构性存在的男性的审视、评判或者侵犯性的男性指责 , 无疑会对女性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伤害 。 在我这里 , 它同时内化为自我的审视 。 像某种分裂 , 始终有另外一个自我 , 极端挑剔和怀疑地观看着“我”的时时刻刻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外婆拔“刀”,母女只剩命苦!记戴安娜这位同在宫里的亲戚!
- 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逝世25周年前夕,车祸豪车下落不明,车主要求“物归原主”
- 离婚一年后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起因竟是女王手写的离婚信?
- 一场完美的婚礼 干货分享,解锁婚戒佩戴的正确姿势!
- 戴安娜|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42岁董洁下地干农活,徒手捏虫子不戴手套!对比王艳差距就出来了
- 作者:黎荔从来不喜欢穿金戴银 童年时代的耳环
- 戴大爷的儿子戴伟早些年为了钱 父亲去世后,戴大爷把三十万存折全给了自己的侄儿
- |拉风!梅西夫妇约会共进晚餐,梅西戴百万百达翡丽鹦鹉螺,安妞拎香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