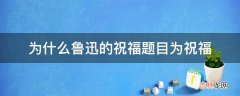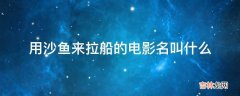新京报:对于中国的学术界 , 你有相关的观察吗?
戴锦华:在中国的学术界 , 我的观察是 , 随着人文学科地位的整体下降 , 女学生的比例持续大幅提高 , 而女教授的比例却没有对应的增长 。 青年女性学者的工作与生存状态相较于替代男性 , 也远为艰难 。 这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趋向有关 , 但我仍相信 , 它也只能经由女性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来改变 。
新京报: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期待一个女性的学术传统 , 我们期待的是对于男性主导的学术系统的反思与改变 。
戴锦华:是的 。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 我也想再补充一些经验性的体认 。 从1993年到现在 , 我在北大工作近三十年了 。 在北大的全部学术生涯当中 , 我始终极大地受益于长辈、同代的女性学者的庇护、提携 , 我得以任情任性地工作和生活 , 在很大程度得自他们的庇护、支持与认可 。
最近一些事件和机遇 , 使我与北大的优秀女学者相聚 , 那些快乐的、互认的时光令我梦想某种实践姐妹情谊的知识共同体 。 它事实上存在于我的生命中 , 我也梦想它最终构成某种结构性变化 。

本文图片
戴锦华与学生在一起 。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
3.3
女性主义的自觉越来越强 ,
女性整体的生存状况却在恶化
新京报:从学术到更广阔的社会 。 你如何看待近年来性别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热潮?我记得你也多次提到过 , 到了今天 , 20世纪后半叶社会反抗运动的三大主轴——阶级、种族与性别当中 , 只有性别是硕果仅存的领域 , 其他两者的批判性和明晰性基本被摧毁了 。
戴锦华:我的整体观察并不乐观 。 当我们在整个社会场域当中看到性别议题凸显的时候 , 并不简单意味着性别议题的热度与关注度的上升 , 必须看到 , 相对于其他严峻急迫的议题而言 , 它尽管同样遭到潜抑但仍然凸显的原因之一 , 是因为它是近乎唯一一个可说/允许言说的社会议题 。 因此它在诸多沉默中成了一个声音响亮的所在 。 对我 , 它固然曝光了女性遭遇的社会问题 , 但它也是多重社会问题与情绪的迸发处 。
形成我的疑虑与保留的另一个原因 , 是今日文化生产的结构和格局 。 文化生产大幅地为资本统御并覆盖 , 具有文化消费欲望与(尤其是)消费能力的人群因此获得了凸显 。 这使得整个城市新中产青年文化消费群体的趣味、需求和愿望 , 以市场意义上的谈判资格的形态得以显影 。 而构成这一社会群体的一代人诞生在独生子女的时代 , 这意味着一个没有先例的社会结构性事实:中国近一半家庭中只有女孩子 , 这构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与性别相关的繁复的文化与心理事实 。 暂且搁置对这一问题的展开 , 我们明显看到 , 女性的文化消费欲望与她们相当高的消费能力直观地影响了文化市场的格局 。 “女性向”甚至超越了性别区隔自身 , 改变着文化惯例与性别定式 。

本文图片
电影《爱情神话》剧照 。
在世界范围之内 , 我们可以看到 , 始自J.K.罗琳、吸血鬼女巫团、韩国的女性编剧群体 , 从另一线索上看 , 则是始自日本家庭主妇的同人创作 , 姑且不展开近来女导演对国际重要电影奖项的包揽——女性在流行文化的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 。 这是一个女性文化崛起的年代 , 还是平等之路上的一次曲折?事实上 , 世纪之交的数十年内 ,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家庭主妇成为流行文化生产中的明星角色 , 这一文化现象并非个案 。 稍作细查 , 可以发现这一现象背后的确是世界性的性别结构的演变与曲折:二战后 , 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女性终于得以进入大学 , 接受高等教育 , 但大学毕业后多数女性却因为婚姻与家庭的社会构成与经济结构延续了成为家庭主妇的社会宿命 , 其教养、文化程度与其社会角色的不对称 , 最终造就了这一文化生产群体的“浮出历史地表” 。 这显然不是简单地用进步/倒退、解放/奴役的逻辑所可以概说的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外婆拔“刀”,母女只剩命苦!记戴安娜这位同在宫里的亲戚!
- 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逝世25周年前夕,车祸豪车下落不明,车主要求“物归原主”
- 离婚一年后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起因竟是女王手写的离婚信?
- 一场完美的婚礼 干货分享,解锁婚戒佩戴的正确姿势!
- 戴安娜|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42岁董洁下地干农活,徒手捏虫子不戴手套!对比王艳差距就出来了
- 作者:黎荔从来不喜欢穿金戴银 童年时代的耳环
- 戴大爷的儿子戴伟早些年为了钱 父亲去世后,戴大爷把三十万存折全给了自己的侄儿
- |拉风!梅西夫妇约会共进晚餐,梅西戴百万百达翡丽鹦鹉螺,安妞拎香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