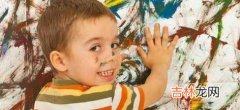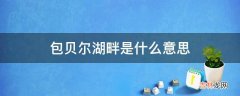焦姣评《白人的工资》︱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必须是白种男人?( 四 )
白种工人也塑造了十九世纪大众文化中的“黑人”形象
既然白种工人是“自由”“独立”“男性气概”和“公民精神”的化身 , 黑人就必须被塑造成另一种形象 。 虽然在政治生活中 , 法律上的黑人奴隶制已经被内战终结 , 但种族主义在大众文化中以另一种面貌存续下来 。 在十九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 , 白种工人文化塑造的自身形象恰好迎合了资本主义劳动纪律对“工人”的规训 。 新生的工业生产秩序要求劳动者勤奋专一、热爱工作、有时间观念、能够约束欲望、推迟满足与享乐 。 当白种工人不得不接受这些劳动纪律时 , 他们将自身对于前工业时代生活的怀恋移情到黑人身上 , 将黑人想象成那个纵情酒色、懒散闲适的曾经的自己 。 用历史学家乔治·拉威克的话说 , 十九世纪的白种工人在想象黑人生活时 , “就像一个改过自新的罪人遇到了从前一同纵情享乐的朋友一般” 。 在白种工人的想象中 , 黑人是他们既鄙视又怀念的前工业时代的化身 。
这种混合了阶级与种族要素的文化想象通过十九世纪的大众娱乐普及到了工人阶级之中 。 十九世纪底层工人中最流行的舞台表演形式之一是“扮黑脸”(blackface)和“黑人歌曲”(coonsongs) , 这些表演在形式上模仿黑人 , 但其主题并不是南方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 。 这些涂成黑脸的白人演员可能扮演各种边缘的角色和有争议的题材 , 他们是花花公子、懒汉、浪荡子甚至异教徒 , 他们抨击政客、讽刺唯利是图的商人、嘲笑宗教卫道士 , 扮黑脸可以使用高雅文化中无法出现的粗俗语言和性暗示——这是一种底层白种工人借“黑人”之口、以戏谑而安全的方式冒犯资本主义秩序的表演 , 它表达的实际上是白种工人自身时刻感受却又无法明言的失落与愤怒 。 这类表演形式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下:自革命以后 , 真正的黑人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出了白人的庆典 , 而在工业秩序的压抑下 , 白人表演者只能使用“黑人”形象来表征自身文化记忆中狂欢与放纵的角色 。 而在扮黑人表演中 , 白人表演者往往又要时刻跳脱出来 , 提醒观众他们只是“扮作黑人的白人” , 唤起白人观众对自身“白人身份”的庆幸感觉 。
十九世纪白种工人塑造的黑人形象显然并不能反映黑人奴隶的真实生活状态 。 晚近美国的“新资本主义史”研究证明 , 内战前南部种植园的奴隶生活并不比北部工厂更闲散 , 种植园对奴隶劳动者的管理同样是高度纪律化的 , 甚至有部分历史学家主张 , 北方的工厂管理者反过来学习了南部种植园的田间管理经验 , 在这个意义上 , 南部种植园奴隶可能比北方工厂里的劳动者更早地成为了现代“工人” 。 美国历史中另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爱尔兰裔和德裔移民工人的“种族”问题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更早来到北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人都认为 , 爱尔兰裔和德裔算不上真正的“白人” 。 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 , 而是因为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想象中 , 爱尔兰裔和德裔移民都沉迷饮酒赌博 , 不具备真正的白种工人的德行 , 因此也不配拥有跟其他白种工人一样的政治权利 。

文章图片
1850年代的政治漫画:爱尔兰和德国移民偷走了美国人的投票箱 。
研究历史上的“白人身份”能帮助我们避免认知中的“白人盲区”
至此 , 罗迪格讲述了一个美国革命时期至内战前后 , 白种工人如何将美国主流的阶级语言种族化的故事 。 无论白种工人的“独立”“自由”“勤奋”“男性气概” , 还是黑人奴隶的“懒散”“愚蠢”“滑稽”“沉溺欲望” , 都是十九世纪白种工人的想象产物 。 罗迪格并不希望将白种工人塑造成“加害者”的形象 。 在他看来 , “白人身份”是白种工人用以应对工业化困境的机制 , 他们既“惧怕依赖于雇佣劳动 , 却又必须遵守资本主义运作机制” 。 对于这些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只为摆脱旧大陆的等级压迫、寻求自身有限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的白人移民而言 , 被工业化生产秩序裹挟是一种痛苦的丧失经历 。 没有人是为了一辈子在工厂里拧螺丝而来到美国的 , 接受自身的“雇佣工人”身份 , 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美国梦”的失落 。 对于白种工人而言 , 种族主义是一剂略带甜味的毒药 , 能够帮助他们饮下工业化的苦果 , 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人世间|近5年高口碑“影视神曲”:《卡路里》排第7,《人世间》排第2
- 清热生津|人间烟火里总藏着美好与希望,听王晰唱《平凡又美好的晚上》
- 南海归墟|《昆仑神宫》之后,跳过《黄皮子坟》直接拍《南海归墟》合适吗?
- 像傻瓜一样去爱歌词 像傻瓜一样去爱歌词是什么
- 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暗含法国知识女性阅读史
-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都学什么 就业前景好吗
- 裤子 光遇:曙光季毕业礼测评,裤子发型和斗篷,会成为经典吗?
- 林志炫|《我们的歌4》林志炫、黄霄云成功配对,高能炫技适配度满分
- 火星引力的新书是什么 火星引力的新书是什么名
- 詹雯婷|《我们的歌4》张远真诚邀请,詹雯婷感动落泪,灵魂碰撞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