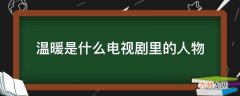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于女性而言,“听话”是最没有想象力的
从一个故事开始吧 , 是我在一个公号上看到的 。 经济富裕的母亲花钱给女儿买了一间30万元的铺子 , 女儿却不领情 , 整天不着铺 。 她不学习、不减肥 , 甚至不看铺子 , 热衷于谈在外人看来一无是处的男朋友 。 母亲上网求助 , 写下事实本身 。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简单乏味 , 即使作为创作素材 , 也看似没有多大的想象空间 。
然而 , 母女故事、平凡生活、隐秘的内心角落、被规定和安排的人生 , 都是这个故事里可以被叙述的潜在元素 。 女儿是真的快乐 , 还是看似叛逆?她在期待什么?她的期待和母亲的期待又有着什么错位?同一条街上还会有其他的铺子 , 20岁出头就当上老板的女儿 , 和其他通过婚姻成为老板娘的中年女性 , 其心境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
女性角色可以局限在私人空间里 , 江南水乡、小巷、古镇 , 是我们所熟悉的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代文学的某种叙事 。 也可以进入职场 , 《陀枪师姐》《壹号皇庭》《妙手仁心》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影视 , 其职业女性的形象 , 在专业领域、工作能力、浪漫都市爱等方面 , 塑造了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生活想象 。 然而 , 只有憧憬 , 并无共鸣 , 因为它并非写实主义的 。 生活的细节该当被分解 , 像侯孝贤电影中回忆往事时的长镜头 , 以及许鞍华天水围日夜里吃不完的三餐 。 我们聚焦具体的生命个体 , 探讨的是女性从私人空间出发 , 进入公共领域 , 之后在二者之间逡巡徘徊 , 寻找自我位置的处境 。

本文图片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 [日]上野千鹤子、[日]田房永子著 , 吕灵芝译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21年9月 。
上野千鹤子的新书 , 标题、封面设计、采用的对话体裁 , 都更接近于科普通俗化 , 放在她之前出版的《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后 , 契合着标题“从零开始” , 类似于某种隐喻 。 尽管我们已经走了一些路 , 但现实的复杂性随时会要求我们回到原点 。 这是集体环境的命题 , 也是理解个人处境的策略 。
从“零”开始 , “零”的起点却因人而异 。 我们需要具体地、不断地认知 , 才能开始我们的反思 。 而进入实践领域的理解与行动 , 是更困难的事情 。 不过 , 如果你足够幸运 , 同时是一个创作者 , 那么你将拥有另一重使命——叙事 。 它将增加一个角度 , 去帮助你激发更大的理解与共情 。
认知:结构下的“不听话”
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 既作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局限的入门读物 , 又在此之上有所拓展 , 它用几个概念来阐释女性同时置身于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下的困境 。 “爱”和“母性”是被建构的神话 , 实际情况是背后所隐藏的经济和权力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矛盾、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双重视角下的“家务劳动”、“中断——再就业”的陷阱等等 。

本文图片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 [日]上野千鹤子著 , 邹韵、薛梅译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20年3月 。
读书时随文写字的习惯 , 有些会成为自己重读时不知所云的感叹 。 重读《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 我看到自己写满了“要看到希望”之类的表达 , 到书的后部就消失了 。 在具体的现实发展中 , 旧有的阐释术语显示出自己越来越大的局限 , 面对新鲜而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 , 我们需要新的语言 。
这当然是“女性写作”某种巨大的意义 。 “女性写作”“女性叙事”在学术表达上无疑并不够严谨 , 但它的意义在于被命名本身 。 我们几乎不谈“男性写作” , 而从性别维度强调“女性” , 在于汇集目光的必要 。 “我们不要互相背弃 , 我们是受到伤害的整体” , 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借主人公之口脱口而出的话 , 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声音 。 在结构性的约定俗成和限制下 , 各种艺术门类的“女性叙事”都会被置于文化边缘 。 在主流叙事之外的个体经验表达 , 会被定义为不够体面的“自传”或不痛不痒的小叙事 。 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内心和声音 , 会以另外的阐释方式被遮蔽 , 狭窄的生活、作品的缺陷、对自我的反叛等等 。 而涌现出的“女性榜样”也变得孤立了 , 我们赞美她的同时 , 赞美的是一个成长的孤立的天才式个体 , 我们看不到群体命运改变的可能性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阿富汗与不同国家商业体系
- 深爱不纠缠,是我赠给你的最后的温柔与疼爱
- 小熊与白生文字中一样的句子:花自向阳开人终向前走,是巧合吗?
- 西京|《镜·双城》西京云沫:此生与君相爱,不负空桑,更不负这份深情
- 本文转自:广东政法春节前夕本该是收拾行装回家团聚的日子脚步却突然被病毒羁绊春运路上人潮与...|防疫路上,这些瞬间让人泪目!有一种力量,无人能
- 徐若瑄|徐若瑄弟弟与她视频落泪,心疼姐姐低谷期,称好久没见她笑了
- 谢娜 太尴尬!谢娜官宣与何炅再次合作,被网友吐槽离开何老师就活不了
- 重读《老人与海》:善良或是多变?硬汉精神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
- 星座|2周后,青山不老,与君白头,3星座旧爱回首,牵手到永远
- 今天才知道,对人体最有害的情绪,竟然不是愤怒与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