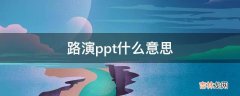香港岛|流浪者们,住在香港150米地下道里:为了省钱娶妻,在地下道生活( 二 )
目前母子二人的生活来源 , 一部分要依靠慈善机构 。 香港有很多慈善机构 , 大多是宗教组织设立的 , 也有私人创办的 , 慈善机构用筹募来的资金建流浪者之家 , 但位置有限 。 所以他们经常定期到流浪者聚集点 , 派发食物和生活用品 。
失业后的娜琳依然在地下道里积极生活 。 她每天会长时间待在地下道 , 为儿子准备一日三餐 。 她身后一米高的柜子里 , 整齐码放着果汁、咖啡和调料 , 还有五颜六色的干面条团 。 炉灶和炒锅架在长桌上 , 她常常用锅煮面条 , 再炒个青豆火腿肠 。

本文图片
图 | 娜琳家的炉灶和炒锅
这些食物有的是慈善机构免费派发的 , 有的是她儿子打零工挣钱买的 。
住在娜琳旁边的邻居很神秘 , 我从未见过她 。 她用白色纸板圈了个院子 , 黑色蕾丝内衣晾晒在院子里 , 每次经过那里 , 我总在想 , 内衣会不会诱发流浪汉侵犯主人 。 但娜琳告诉我 ,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
生活地下道里人 , 他们互不打扰 , 也互不关心他人 。 这不算冷漠 , 他们为了应对自己的生活 , 就已经花光所有力气 。
“至少生活在这里很自由 。 ”白发苍苍的印度老婆婆对我说 , 她走路略微弓腰驼背 , 说英语丝毫不带印度口音 。 她一边把五六个盛满水的塑料桶摆放整齐 , 一边告诉我 , 这是她从跑马地外的公共卫生间里接来的水 。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 , 来来回回好几趟 , 她看上去已精疲力尽 。
印度婆婆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 , 已经忘记哪年来的 , 也不愿透露此前的经历 , 又是怎么成为流浪者的 。 在地下道里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 如果对方第一次不愿说 , 那就永远不可能知道 。
印度西部是10月底过印度新年 , 共持续5天 。 白天 , 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地的单身男子 , 会到距离地下道50米的印度锡克庙吃免费的餐食 。 锡克庙的免费餐食所有人都可以吃 。 夜晚 , 他们到锡克庙参加庆祝活动 , 载歌载舞 。 结束后 , 他们回到地下道 , 撑开各自的旅行帐篷 , 钻进去睡觉 。
那天我碰见印度婆婆 , 祝她新年快乐 。 她笑着说 , 有钱天天是新年 , 没钱新年和自己也无关 。 那几天锡克庙举办活动 , 印度婆婆一次也没参加 。

本文图片
几年前 , 我从内地来香港工作 , 赛马场地下道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 。 不赛马的时候 , 跑马场是个运动场 , 可以跑步 , 踢足球场 , 打曲棍球 。 下了班 , 我常途径地下道 , 到跑马场上跑步 , 因此经常会与住在这里的流浪者们交流 。
“马场地道”的设计初心 , 是为了在喧闹的赛马日分流观众 , 并不是为了行人通行 。 除了每周三的赛马日 , 平时少有行人路过 。 这恰好为流浪者提供了在此安营扎寨的有利条件 , 此地常年居住着不同国籍的流浪者 , 是香港露宿圈中小有名气的“联合国村” 。

本文图片
图 | 马场地道一角
这里并非是个无人监管的安乐窝 。 香港警察会不定时到访此地 , 抽查流浪者的身份证明 , 证件合法且没有窝藏违禁品 , 就可以继续居住 。 前提是 , 要自觉靠西侧安家 , 面积大约占据地道的三分之二 , 剩下三分之一约有一米二宽 , 足够行人通过 。
每逢酷暑、冬天或是台风天 , 特区政府都会开放社区中心 , 让流浪者留宿 。 但一年中这样的日子为数不多 , 他们去过几次便不愿再去 , 仿佛地下道才是他们长久的归宿 。 而且一旦离开 , 他们的领地很可能会被其他流浪者占领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米饭|你有多久没吃到米饭香了?
- 葛薇龙|三刷《第一炉香》:明知道乔琪不爱自己,葛薇龙为何还要嫁给他?原因有三
- 天下第一奇庙”!不供仙佛,却供27位解放军,每日香火鼎盛
- 香蕉|男生嘴馋,偷吃女同桌的香蕉不承认,结果被发现,好戏上演了
- 老人|一位七旬老人的晚年:退休金8000,在儿子家被当成香饽饽
- 杨云香|微醺的脸颊,朦胧着眼
- 社会怪象:年轻人不要996,却偏爱临时工,工资日结这么香
- |50岁藤原纪香“胜利卷”亮相,V领让人视线不自觉下移,腰细腿长天鹅颈
- 李培香|四川农民被冤“杀妻”,蒙冤21年寻妻耗资百万,通过卧底揪出前妻
- 关于生活的治愈系文案:不必太张扬,是花自然香,是爱自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