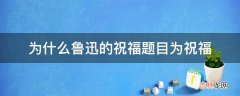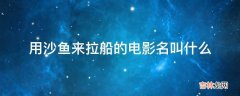【约翰尼·德普|德普案中的厌女狂欢,与美国保守主义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扑】被劫持的性别话语——女性主义的分歧
“我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 但我反对艾梅柏 。 ”艾梅柏败诉后 , 舆论中许多女性主义者弃之如敝履 , 认为她的个人表现存在缺陷 , 她的败诉损害了Metoo运动 , 因此并不支持她 。 另有Metoo运动的支持者认为“女人才是家暴受害者”是一种性别歧视的刻板印象 , 并不仅仅存在男性打女性的情况 , 女性也可以是家暴的施暴者 , 男童、老年男性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 且更加隐匿 。 而在本案中 , 德普才是受害人 。

本文图片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7日 , 美国弗吉尼亚州 , 艾梅柏·希尔德(Amber Heard)离开费尔法克斯法院 。
首先 ,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家暴受害者的出发点是合理且有必要的——男人当然可以是家暴受害人 。 反性侵并不要基于性别的筛选才能得到Metoo运动的支持 。 但是 , 提出这个先进论点的女权主义者也应该意识到 , 一个虚伪的女人、一个前后不一致的撒谎女人、甚至另有所图的贪心坏女人 , 在理论上 , 也可以是家暴受害人——反性侵运动中 , 一个女性并不要通过了“好女人”或“坏女人”的人格筛选才能得到Metoo运动的支持 , 才能反家暴 。 换言之 , 一个人的性别和人格 , 与是否经了家暴不一定直接相关 。
有了“家暴受害者不一定非要是女性”的出发点 , 我们当然可以提出“艾梅柏家暴了德普”的假设并且进行合理怀疑 。 但是 , 在“他说vs她说”的孰真孰假判断过程中 , 问题的本质依然要围绕家暴是否发生的事实来做判定——我们仍需要求诸于法律程序来执行性别的正义 , 真相不辩不明 。 同时也要承认 , 现实中的家暴举证困难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 当直接证据不足、显性的证据有限的情况下 , 双方个人品德、行为历史和支持资源等 , 才作为间接证据提供参考 。 正因为举证困难 , “谁是家暴者”的问题只能是“谁更可能是家暴者”——一个“实然”的真相问题只能让步于“应然”的主观判断 。 这时 , 我们应该相信谁?尤其是在媒介操纵 , 信息污染 , 在结构性不平等是一个社会既成现实条件下 , 我们选择相信谁?
在德普和艾梅柏之间做判断时 , 我们显然遇到了一种具有讽刺性的困难 。 “22条军规”的圈套已经无数次发生在现实中的反性侵案的申诉者身上了 。 正如艾梅柏的律师在最后的辩论中称:“如果你没有拍照 , 那么家暴就没有发生;如果你拍照了 , 那么照片就是假的 。 如果你没有告诉你的朋友 , 那你就在撒谎;如果你告诉了你的朋友 , 他们也是骗局的一部分 。 如果你没有求医验伤 , 那就没有家暴;如果你验伤了 , 那你一定是疯了 。 如果你定罪或者反击 , 那么 , 你才是真正的施虐者 。 ”正如《纽约客》把艾梅柏的举证过程比喻做“咬尾蛇”的死循环:任何自证清白的行为反而都证明了你是有罪的 。
如果真正平等地看待男性受害人和女性受害人 , 必须追问这样一个现象 , 艾梅柏在反家暴举证中遇到的死循环是否发生在了德普的身上?如果没有 , 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二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金钱、性别和社会资源等结构性不平等又能否真正支持我们“绝对平等”地看待他们?且不论任何政治观点阵营和立场 , 看客能否放下先入为主的概念 , 排除信息干扰的同时又打破信息蚕房 , 放下自身的道德优越感 , 来保持判断?有时那些越是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是公正法官的人总是会不慎沦为荡妇羞辱的帮凶 。 围观者不一定能成为法官 , 但如何不沦为帮凶?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南京胖哥|南京胖哥谈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别说女性,男的也经不起这样暴打
- 人这一辈子 一段人生,如果只有一条路,一种选择,一个答案
- 如果你问另一半对婚姻什么想法和态度?如果Ta给你一个相对完美的答案 婚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凑合着过日子
- 如果你问另一半对婚姻什么想法和态度?如果Ta给你一个相对完美的答案 如果你问另一半对婚姻什么想法和态度?
- 用最简单的文字 没有找到答案,就很难做到,会是透明的
- 是什么在影响我们的情绪?大部分人的第一答案是生活 决定情绪的,到底是事情本身,还是我们自己?
- 什么样的人会让异性永远保持新鲜感?网上众多真实案例中 什么样的人会让异性永远保持新鲜感?
- 不言不语,是不是最好的答案
- 我最近接到一个案例 男生和女生吵架后,为什么会沉默?
- 拿得起 一个人,放下了你,眼神里,总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