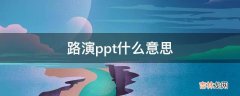戴锦华:对 。 可以说类似认知成了我参与第三世界调查的动力 。 也可以说第三世界调查中的见闻构成了这类认知形成的经验性力量 。 当左翼知识分子还没有能力去回应“大失败”的时候 , 第三世界的行动者已率先回应 。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萨帕塔运动”(Zapatistasmovement) 。 1994年 ,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签署日 , 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 , 2000多个原住民拿着极少量的武器、更多的木头枪、镰刀和斧头出现在州首府街头 。 他们呼喊着“受够了就是受够了”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 。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得意洋洋的冷战胜利者宣告:一切还没完!
深入第三世界腹地、与反抗者和行动者同在的这些岁月对我的一生弥足珍贵 。 但就思想和学术的预期而言 , 我所谓的失败也发生于此 。 因为整体预期中最重要的 , 一是在遭压迫最深重的人们那里找到新的行动的可能性 , 二是一个极为天真的设想——在未被欧美思想、理论玷污的第三世界获取别样的知识、思想与资源 。 类似的诉求在我们持续地、不断深入地对亚非拉诸国的乡村、腹地、运动现场的考察中 , 我的天真的预期遭遇了最大的失败 。
我常提到的例子是:在古巴哈瓦那切·格瓦拉研究中心——也是切·格瓦拉的故居 , 在他的书房的书架上 , 我看到一部他反复阅读、边角都卷起了的书籍是法文版的《阿尔都塞文集》 。 我曾经以为我昔日的理论脉络 , 是包括阿尔都塞在内的法国理论 , 而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抗则发生在它的平行线路之上?我自己不觉苦笑的是 , 我早已经知道阿尔都塞的学生、今天法国的有机知识分子德布雷是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成员 , 但我仍天真地构想游击中心论/切·格瓦拉主义是那一格局之外的“洁净”的存在 。
《论再生产》 , [法]路易·阿尔都塞著 , 吴子枫译 , 西北大学出版社 , 2019年7月 。
但比类似自我嘲弄更为深刻的感受是 , 殖民统治绝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的统治 , 也是文化的摧毁 , 曾经差异性的地方知识与文化被暴力毁灭 , 令第三世界经历着精神上的赤贫与效颦 。 序号第三原本接续着序号第一、第二而排列 。 资本主义的全球版图不断地消灭着外部与异类 。 所谓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正因此而诞生 。
这是我的失败 , 也是我的获知与获得 。
为此 , 产生了我的学术成果:“萨帕塔运动”研究 。 我是编纂与翻译 , 也是学习与理解 。 我们抵达恰帕斯 , 重返恰帕斯 , 与当地的行动者、学者、原住民共处、访谈、请教 。 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展开了对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研究 。
《蒙面骑士》 , 戴锦华/刘建芝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6年6月 。
新京报:在方法论层面 ,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启 , 还有你曾经提到的政治经济学转型 。 你现在依旧认为那是一个失败的转型吗?
戴锦华:所谓政治经济学转型 , 与其说是失败 , 不是说是放弃 。 放弃的原因不是跨学科 , 也不是学术的难度 , 而是我发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科学和我的构想间存在着落差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社会科学是建构性的功能性学科 , 服务于社会的主体结构 。 因此 , 相对于人文学科 , 似乎是后者包含了更大的反思和批判的可能性空间 。 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 , 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给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维度和助力 , 但我的选择是借助社会科学 , 在他们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 。
这三条路径 , 或者说三个面向的追寻 , 相对其最初的预期 , 都可谓落空或失败了 。 但当我再度开启自己在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工作时 , 这一歧路或弯路显现出始料未及的意义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外婆拔“刀”,母女只剩命苦!记戴安娜这位同在宫里的亲戚!
- 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逝世25周年前夕,车祸豪车下落不明,车主要求“物归原主”
- 离婚一年后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起因竟是女王手写的离婚信?
- 一场完美的婚礼 干货分享,解锁婚戒佩戴的正确姿势!
- 戴安娜|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42岁董洁下地干农活,徒手捏虫子不戴手套!对比王艳差距就出来了
- 作者:黎荔从来不喜欢穿金戴银 童年时代的耳环
- 戴大爷的儿子戴伟早些年为了钱 父亲去世后,戴大爷把三十万存折全给了自己的侄儿
- |拉风!梅西夫妇约会共进晚餐,梅西戴百万百达翡丽鹦鹉螺,安妞拎香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