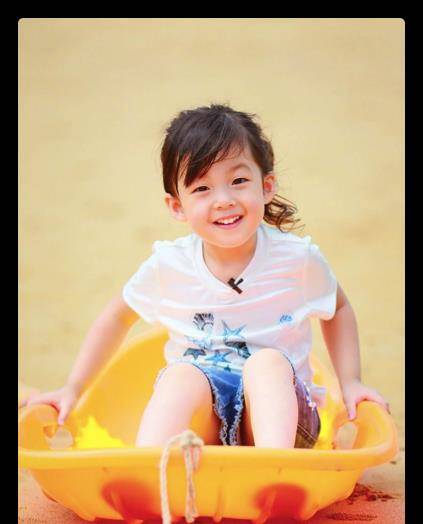本文图片
戴锦华 。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
所谓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如同昔日的女性主义一样成为我内在的视野或者说是观照角度 。 更重要的是——我的确满怀感激和自豪 , 当我再次投入中国视野 , 再次投入电影研究与文化研究之时 , 我可以笃定地说 , 我拥有了世界性视野 。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 我们一直在追求将我们的视野拓展向世界 , 但彼时我们所谓的世界视野始终是欧美视野 , 进而是欧美视野加(与)中国视野 。 当我以自己的双脚走过如此多的第三世界国家 , 尤其抵达如此多基层与现场之后 , 我相信自己对于世界的整体与真实状况、对于现代世界的理解 , 对当代中国 , 对理解和进入西方思想史、如何放置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的相互位置 , 有了自己的真切的、知识与经验的参数 。
例如 , 我可以知道 , 当我们说在非洲思考、在亚洲思考、在拉丁美洲思考时 , 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 在这样一个曾经是以欧洲为中心 , 此后是北美君临的世界格局当中 , 每个区域处于什么样的相对位置 , 其困境与可能何以形成 。 同时 , 在具体的问题上 , 比如某一波电影新浪潮的发生 , 某一个非西方导演的成名 , 我会有迹可循地去发现其与文本脉络相关的社会事实与国际互动逻辑 。
当我重新恢复了频繁的国际学术旅行时 , 我也真切地感觉到 , 在世界各地 , 类似的生命经验不仅受到同行的重视 , 也多少享有人们的羡慕 。 因为我不仅经由学理 , 而且经由经验和视野 , 获取了对世界不同的理解和表述 。
开始时我们提到的危机和应对 , 我说过 , 对我来说 , 这始终不是单纯的或有意识的学术转型 。 这也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对生命、社会与知识的诚实与坚持 。
PART 2.
现实追问:清理债务与反思批判
2.1
当问题的前提条件被改变 ,
我们如何重新追问?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了一些困惑 , 比如批判的意义和可能性 。 到了今天 , 当时那些未能解答的困惑有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答?或者说 , 在这几年 , 你是否产生了一些新的追问?
戴锦华:不能说得到了解答 。 当年的所有困惑 , 逐渐沉淀形成了一些问题系 。 我明确提出了这些问题 , 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 但我同时明确的是 , 多数问题大约无法以一己之力获取答案 , 也可以说真正能回答这些问题的 , 也许不是个人、思想或学术 , 而是历史 。
另外一边 , 近年来全球的变迁 , 已经改变了形成这些问题的前提 , 或者说社会的基本生态已开始有别于我设定问题之时 。 这些改变使得我必须重新修订我的问题系、我的参数 , 甚至我必须要重新提出问题 。

本文图片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
我始终坚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召唤新的历史主体?这涉及两个层面 。 我以为所谓左翼思想者的工作始终围绕于此 , 也受困于此 。 当working class(工人阶级)被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改变与解体之后 , 我们如何去想象和命名历史的主体 , 如何直面并处理阶级论自身所造成、所携带的20世纪历史债务 , 这是一个真问题 。 当然 , 人们做过许多努力 , 比如multitude、Saltern(编者注:庶民) , 多数 , 99%……人们尝试找到一个集合型的对多数的表达 , 一种包容差异性于其间的命名方式 。 但类似命名真的可以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整体性进程吗?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外婆拔“刀”,母女只剩命苦!记戴安娜这位同在宫里的亲戚!
- 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逝世25周年前夕,车祸豪车下落不明,车主要求“物归原主”
- 离婚一年后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起因竟是女王手写的离婚信?
- 一场完美的婚礼 干货分享,解锁婚戒佩戴的正确姿势!
- 戴安娜|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1981年,卡米拉站在戴安娜的婚礼上,眼里藏刀,和查尔斯眉目传情
- |42岁董洁下地干农活,徒手捏虫子不戴手套!对比王艳差距就出来了
- 作者:黎荔从来不喜欢穿金戴银 童年时代的耳环
- 戴大爷的儿子戴伟早些年为了钱 父亲去世后,戴大爷把三十万存折全给了自己的侄儿
- |拉风!梅西夫妇约会共进晚餐,梅西戴百万百达翡丽鹦鹉螺,安妞拎香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