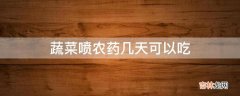1966年的获奖者,“和解”是她的关键词,但唯有深渊中的人才有权“和解” | 姜林静

文章图片
1966年 , 瑞典籍犹太女诗人奈莉·萨克斯(NellySachs)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 。 75岁的她依旧有着少女梦幻般的双眸 , 安静苍白的脸上挂着微笑 , 很难想象 , 人性和诗性的巨大力量会从这样纤弱娇小的身躯里涌出 。 死生的重量 , 随蝴蝶振翅 , 沉落至玫瑰 。
虽然文学在她生命中一直举足轻重 , 但真正的创作 , 却始于年近半百时的流亡 。 1940年5月16日 , 萨克斯带着体弱多病的母亲 , 乘坐离开纳粹德国的几乎最后一班客机 , 从柏林逃亡至瑞典 。 此前 , 她们已在盖世太保眼皮底下胆战心惊地生活了七年 , 并刚刚收到了遣送集中营的召集令 。 极度恐慌中 , 德国挚友为她们申请的瑞典签证也奇迹般地到了她们手中 。 她就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
恹恹的蝴蝶很快又见到海——这块石刻着蝇头楷碑文
交至我手中——(《在逃亡里》)
以色列民族在无路可退时奇迹般地跨过红海 , 萨克斯与年迈的母亲则在绝望无助的最后关头飞越波罗的海 。 在亲历“逃亡与救恩”的过程中 , 象征着犹太教神启的那块石板 , 似乎终于在以色列民族代代相传的宿命中被交至女诗人手中 。
然而 , 逃离死亡的追捕并不直接意味着生命的开端 , 举目无亲的母女到达斯德哥尔摩时 , 唯一的财产只有提箱里的私人物品和少量帝国马克 。 茕茕孑立的最初十年是异常艰难的:“贫穷 , 疾病 , 彻底的绝望!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幸存下来的 。 ”出生于犹太富商家庭的诗人 , 与母亲一起蜗居在斯德哥尔摩的出租公寓里 。 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 , 萨克斯无法外出就职 , 除了做洗衣女工 , 就只能在家翻译瑞典语诗歌 。 她蜷缩在厨房角落一张破旧不堪的桌子上 , 在那里吃饭、睡觉、翻译、写作 , 手稿散落在橱柜里 。
1950年 , 相依为命的母亲在经历长久的病痛后去世 。 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中 , 萨克斯几乎没有一天离开她的母亲 , 这种零距离的共生关系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爱的枷锁 。 “我的母亲死了 。 我的幸福 , 我的故乡 , 我的一切 。 ”这早已不是诗人第一次经历离别 , 但母亲死后 , 极度依恋家庭、渴望联结的萨克斯彻底孑然一身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 独自面对恐惧与胁迫:
哦 , 我的母亲 ,
我们住在一颗孤星上——
最终悲叹出遇死者的叹息——
多少次你脚下的沙消失
留你孤身一人——
……
哦 , 我的归乡人 ,
奥秘随遗忘愈合——
可我听见新的奥秘
在你满溢的爱里!(《哦 , 我的母亲》)
直至花甲之年 , 国际声誉才纷至沓来 。 大世界涌进了小厨房 , 但即使她的名字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 她却始终与成功保持着距离 , 甚至不愿将自己标榜为诗人 。 她在1959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其实我是个实实在在的家庭主妇 , 从来都不是诗人 。 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 ”不过她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但我们女性也可以成为诗人 。 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投入火焰中 , 在最危急的时刻结结巴巴地吐出几个词 。 ”如同一株被绳索与黑烟困住的玫瑰 , 她从未走出恐惧与孤独 , 甚至在字面意义上不背叛过去的生活 。 母亲去世后 , 她依旧独自生活在简陋的出租小屋里 , 除了领奖 , 从未远游 。 经济情况好转时顶多添置几件漂亮的家具 , 她在这里操持家务、接待朋友、创作并翻译 。
大屠杀无疑是她作为诗人的真正开端 , 她甚至拒绝再版1940年流亡前的任何一篇作品 。 这绝非对过往岁月的背弃 , 绝非扭头不直面曾经的伤痛 。 如果说流亡前 , 她的文字里还带着甜蜜的忧郁气质 , 还只是为了疗愈自己而创作 , 那么现在 , 她就是已然死过一回的人了 。 她在死的灰烬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 在毁灭中开始建构自己的宇宙 。 那是诗人的涅槃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对获奖者的赞美句子 关于对获奖者的赞美句子
- 荡口古镇有多少年的历史
- 现存最古老歌曲,竟是公元前1400年的“胡里人圣歌”!(内附视频)
- 男人不愿花10万娶相恋多年女友,转身20万娶相亲半年的对象,太扎心
- 中元节是什么时候 中元节介绍
- 今年是第几个教师节 2022年是第几个教师节
- 岁岁年年什么意思 岁岁年年的意思
- 教师节是几月几日
- 今年是第几个教师节2022年
- 2021国庆放假时间安排 今年的国庆怎么放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