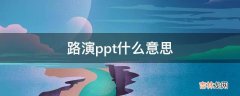……如果我知道 , 你还醒着 , 而且是因为我的缘故 , 我就无法安心写作 。 但如果我知道 , 你已睡下 , 我就会勇气倍增地写下去 , 因为在我看来 , 好像你已经将自己完全交付给了我 。 酣睡中的你是多么无助 , 多么需要人看顾啊 , 就好像我是为了你和你的安好而写作 。
有了这样的想法 , 写作怎么还可能停顿呢?睡吧 , 睡吧 , 白天你的工作比我多多了 。 无论如何 , 你要快点去睡 , 明天请不要坐在床上给我写信了 , 也许今晚也不要写了 , 如果我的愿望足够有力的话 。 而且在你睡觉之前 , 你可以把阿司匹林药片先扔到窗外 。
两种想象 , 两个女性形象 , 一个是保护者 , 另一个是被保护者 。 两者相互矛盾 , 只要卡夫卡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包含两个菲莉丝形象 , 矛盾就无法消除 。 他感受着矛盾造成的压力 , 何时转向哪个形象 , 取决于恋爱曲线发烧般的起伏 。 他轻而易举就能逃避:从一个幻影转移到另一个幻影 ,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阻碍了他去兑现曾再三强调的亲密关系 。
有一回强大的菲莉丝和弱小的菲莉丝相遇了 。 她给他寄了一张童年照 , 大概是她十岁时拍的 , 卡夫卡几乎感动到流泪 。 “肩膀这么窄!她真是弱不禁风啊!”他随即意识到 , 这个女孩就是那个“还未曾解释为何会在酒店房间里担惊受怕的女人” 。 菲莉丝于是又给他寄了一张照片———出于一种微妙的、有点矛盾的妒意 , 谁知道呢 。 这回她寄来的照片上是一位从容笃定的成年女性 。 卡夫卡忽然间就不确定了:
新寄来的照片给我的感觉有点奇怪 。 我觉得自己和小女孩的距离更近 , 我可以对她说任何话 , 而我对照片上的女士却怀有敬意 。 我想 , 即使她的确是菲莉丝 , 她也是长大成人的菲莉丝 , 俨然是位需要认真对待的女士 。 小女孩很有趣 , 她并不悲伤 , 但神情却非常严肃 , 面颊饱满(这也许只是晚上灯光的作用) , 脸色有些苍白 。 如果我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 , 虽然我决不会不假思索直接跑向小女孩 , 我不会这么说的 , 但我也会朝着小女孩走去 , 虽然会走得很慢 , 而且一边走 , 一边会四处寻找女士 , 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 。 最好的情形是 , 由小女孩带着我去找女士 , 并把我介绍给她 。
卡夫卡手里拿着两张照片 , 女孩和女士 , 两人都在看着他 。 他的目光从其中一个游移到另一个 , 他试图重合这两个形象 。 但他无法做到 , 总有一天 , 他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
第三十二章 自我审判:《诉讼》与《在流放地》
卡夫卡的《诉讼》是个庞然怪物 。 里面没任何东西是“正常”的 , 也没有任何东西是简单的 , 无论你是研究它的诞生史 , 它的原稿 , 还是分析其形式、题材、内容 , 或者着力于阐释这部作品本身 , 探究的结果都一样 。 无论朝哪里看 , 都是幽暗一团 。
这一点 , 布罗德最先感觉到了 , 因为卡夫卡经常会给他读上几页 。 最终 , 布罗德把手稿拿回家去了 , 他可不想让卡夫卡把书稿销毁掉 。 他深信《诉讼》是部重要作品 , 足以让好友成为超新星 , 光耀文坛 。 可他最终拿到手的却是松散的一百六十一张活页 , 大部分正反两面都写了字 , 从几个本子上扯下来的 。 卡夫卡给这堆稿纸草草归了类 , 给每一“捆”(可以理解为一个章节)加了一页封面 , 上面写有临时性的标题 。 但是有几“捆”里面仅存一页 , 而另几“捆”则让人怀疑包含了不止一个章节的内容 。 其中哪些章节已经写完 , 卡夫卡在生前从未透露 , 也从未给这些章节编过号 。 所以摆在布罗德面前的仿佛一个大杂烩 , 里面有已经完成的章节 , 快要写好的 , 才写一半的 , 以及刚刚才写了个开头的章节 。 而且如果要做成书 , 布罗德还得自己给这些章节排序 。 当然 , 他还有大把时间、大把机会直接询问作者本人 。 只是对此他很谨慎 , 不轻易开口 。 布罗德很高兴把这个珍宝锁在自己抽屉里保护起来 。 他以一贯的方式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晚春时光,倾城花凉
- 人世间|比《人世间》更动容的是深情:读懂父亲的爱,就读懂了人生
- |重温《隐秘的角落》我才懂徐静“逼迫张东升离婚”,到底有多狠
- |《重生之门》奇奇怪怪的演员出圈方式又增加了,观众直呼长知识
- |重温《锦衣》,才懂陆大人很早就对今夏动心,为何迟迟不表白?
- 春日迟迟再出发|《春日迟迟再出发》成年人的爱情瞻前顾后,想着的是退让
- 春日迟迟再出发|《春日迟迟再出发》面对林承纬的表白,吴雅婷坦白毫无心动是假的
- 《围城》里写道:“婚姻就像一座围城 分房睡对婚姻会有哪些影响?
- |善意的表达着成熟,是心怀善意
- |《亲爱的小孩》:有福之人,有些话从不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