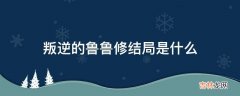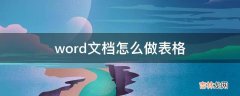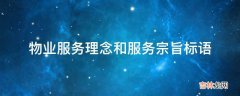自由职业的时间表和上班没太大区别 , 早晨起来吃早点 , 喝杯咖啡 , 坐在电脑前工作 。 写作其实很需要这种枯燥的节奏感 。 写得顺的话 , 一个月能写完一篇 , 有时需要两个月 。 写作的时候常常感到痛苦 , 过后总不记得 。 先生说我那时候天天在家哀嚎“不会写怎么办” 。
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以后要干这个 。 有次被家里大人罚站 , 我低着头在墙角哭 , 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 落在脚尖 , 成了一个个黑色的小点 。 它像什么呢?我想把它描写出来 。 有了这个念头后 , 罚站变得不再重要 , 把它记录下来才重要 。 对小孩来说 , 那是个很奇怪的经历 。 好像找到了止痛的方法 , 突然有一瞬间 , 我感到痛苦消失了 。
其实我比较晚慧 。 和下棋一样 , 这种靠天分吃饭的行当一般是“20岁不成国手 , 终生无望” 。 文艺的天赋也是早早就体现出来了 , 张悦然、周嘉宁她们十八九岁已经出名 。 我到二十多岁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要写什么 。
研究生毕业后 , 我做过两年电影采访人员 , 当时明确自己不可能一直做这份工作 , 自由写作的时期一定会到来 , 或早或晚 。 做采访人员期间也有文学杂志的编辑向我约稿 , 后来算了一算 , 照自己产出的速度 , 到手的稿费基本可以与工资持平 , 我就辞职了 。
那个时候我没有奢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小说作者 , 小说是非常难写的 , 需要熟练的技巧 。 刚开始写散文 , 总想着写出一些奇观 , 大家才有兴趣看 。 但我是个普通人 , 经历乏善可陈 , 写着写着就发现 , 我并不那么习惯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生活 。
《如雪如山》出版之前 , 我写过几本幻想类小说 。 当时善于将想象作为灵感 , 在某个地方读到的一句话便可以成为一个故事的出发点 。 本来习惯了躲在角色背后 , 可是到了这本 , 好似被人往前推了一步 , 作品被评判的同时还要被拿来与作者联系起来 。 许多人问我女性作家的书写经验 , 以及 , “在生活中有哪些因为性别而经历的压抑体验?”
好像躲闪又失败了 。
其实 , 我更愿意做一根导管 , 或是一双摊煎饼的手 。 希望大家享用导管从神秘泉眼引过来的甜水、夹了果篦儿的煎饼 , 而不在意那根导管是什么颜色的、摊煎饼的手是胖是瘦 。
“说句话容易 , 过生活太难了”
《如雪如山》的七个故事里主角名都叫作“lili” , 之前我有本中篇《荔荔》 , 后来又写了一个Lily的故事 , 故事背景设定在国外 。 不自觉地 , 发现大家都叫“lili”——这个名字很美 , 又很普通 , 漫不经心的 , 很像一对父母随手赋予一个女孩的名字 , 乍听起来就不属于那种很明艳、醒目的女孩 。
书中几个篇目来自约稿 , 有篇主题是女人的生活 , 于是写了《地上的血》 。 写的时候 , 内心有过好一番缠斗 , 经血这事似乎过于琐碎 , 我到底要不要写?这个故事的戏剧价值有我认为的那么大吗?每次脑袋闪过这些念头时 , 身体里分裂出的另一个老张就会劝自己 , 写吧写吧 。 不管顺着那滴小小的血拉拽多少次 , 都会拽出同样的、庞大的、不可忽视的哀伤 。
还有一篇约稿的主题词是纪念日 , 直到现在 , 《纪念日》最后那部分我还是不敢看 。 那个充满尿味、马桶上有粑粑点点的卫生间是我创造出来的 , 我很清楚它有多难闻 。 实在不想再次回到那个卫生间去了 。
你可能觉得头一篇《我只想坐下》太拖沓 。 写的时候 , 我希望给读者营造一种在火车上昏昏欲睡的节奏 。 你知道的 , 坐车时总是睡了一觉睁开眼后发现仍在原地 , 进度条像被卡住了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大张伟|《我们的歌4》大张伟无效谐音梗,许靖韵听不懂,林海束手无策
- 张翰|他是帅到连霸总张翰都自卑的男二?网友扒出照片:到底啥样啊
- 男友|跟男友旅游N次,一张好看的照片都没有。
- 詹雯婷|《我们的歌4》张远真诚邀请,詹雯婷感动落泪,灵魂碰撞值得期待
- 姜超|姜超妻子张蒨:普通职业嫁明星丈夫,恩爱多年生一子
- 张馨月|张馨月和家人出游,与林峯父母搭肩合影相处融洽,婆媳比心像闺蜜
- 陈小春|陈小春、张智霖无奈选择丢卒保车,刘恺威出现错觉,又惨又好笑
- 塔罗|塔罗:默念对方的名字替他选张牌,离开你之后他有后悔吗?
- 周亦安|《底线》周亦安保住了法官的名声,张院长的“破例”好假、好假!
- 周亦安|《底线》第34-35集预告:听到大家要给叶芯介绍对象,周亦安紧张慌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