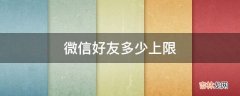新京报:也就是说 , 在目前的个体化2.0版本中 , 我们不存在除了新家庭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外的资源?
阎云翔:理论上讲应该有 , 但是我目前还没观察到 。 既然向传统回归了 , 人们似乎很难在传统内部找到关系本体论架构之外的任何资源 。

本文图片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
个体化或非个体化 ,
与个体的幸福与否没有直接关系
新京报:近年来 ,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指出 , 年轻一代实际上更保守了 。 在有关个体化2.0版本的叙述中 , 你似乎也持有类似看法 。 或者 , 我们不用“保守”这一笼统的词汇 , 而是说面对个体化进程 , 个体在社会行动意义上的能动性是否变弱了?例如 , 抑郁症的流行 , 年轻人自嘲“小镇做题家”等 。
阎云翔:我并不认为个体在社会行动意义上的能动性(agency)变弱了 。 因为能动性实际上就是自我选择 , 根据自己的选择作出行动的能力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如果年轻一代选择听父母的话 , 利用新家庭主义实现自己的目标 , 那也是能动性 。 所以 , 他们的能动性没有减少 , 关键是这一能动性在往哪个方向努力 。 我觉得现在的发力方向就是如何强化自身的关系性存在 , 并且尽一切努力改善使自己的关系性存在有所依托的具体处境 , 例如家庭关系或者职场关系等等 。
年轻一代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特别多的主观能动性 , 比如刚刚讨论过的禅修营例子 , 自己的关系性存在遇到了挑战 , 有了困惑 , 那么我就换一个全新的关系环境 。 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主动的自我探索的选择 , 但依然是关系本体论架构中的选择 。
新京报:我之前看资料时 , 看到你提到过:“个体化进程给个体所带来的“痛苦” , 只是 , 这些痛苦是短暂的 。 我很好奇 , 现在你依旧这么认为吗?
阎云翔:我一直认为 , 个体化与非个体化与个体的幸福与否没有直接关系 。 我也从来不认为 , 个体化展现的是一幅幸福的图景 , 个体解放出来就一定更好 。 东北话说得好 , “炕不能两头热” 。 个体获得自由选择的同时 , 就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 也会面临更多的困境 , 感受到新的痛苦和挑战 。 个体化2.0呈现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式 。 在很大程度上 , 这种解决方式让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人消除了不适感 , 没那么痛苦了 。 与此同时 , 它可能又让另外一部分人觉得更加不适 , 因为他们想沿着个体化1.0的道路走下去 , 结果发现大趋势忽然逆转了 , 当然就会有痛苦、有纠结 。 只是说 , 个体化两个版本所引发的痛苦的人群不一样 。 至于短暂这点 , 就看你怎么定义 , 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 , 十年也是很短暂的 。
个体化也好 , 个体化的传统转向也好 , 我们不要把任何一个方向加以浪漫主义的想象 。 这样 , 你就会发现 , 这种痛苦本质上是纠结 , 纠结在于我们本来是关系性的自我存在 , 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尝试改变这种关系性的存在 。 客观层面上社会结构的个体化 , 既为我们带来诸多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和选择 , 也迫使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主观层面上的个体化 , 则不断地以个体主义价值观向我们得以安身立命的关系本体论和关系性个体存在提出挑战甚至很难拒绝的诱惑(如 , 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等等) 。 对于许多个体而言 , 夹在传统回归与个体化之间的复杂感受又岂是“纠结”一词可以道尽?所以 ,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放弃浪漫想象 , 在本体论的层次开展冷静客观的反思 , 最终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活法或者自我的存在方式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儿女|“儿女的经历,让我明白香火难继的真相”:有些坎,绊倒无数家庭
- 伏尔泰说:“对于亚当而言 一个家庭幸福,藏在三件小事里
- 结婚|结婚,请选择这几种家庭的男生
- |温暖异国外乡人,她带领团队为外籍家庭建起“洋居委会”
- |为啥俩儿子的家庭“不要嫁”?五个理由中一个,女儿的日子不好过
- 家庭主妇|日本70岁阿姨,5点起床做家务,但她的精致优雅却让很多人羡慕
- 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生的,结婚之前你要擦亮眼睛去了解
- 一个家庭幸不幸福 如果一个家庭存在内耗,那未来道路绝对是充满坎坷的
- 人这一生 在家庭能够和颜悦色, 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
- |原生家庭是不是真的能毁人一生?北大教授:造成难以挽救的结局